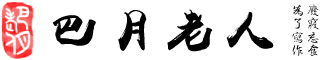一切緣起

神龍井底,竟然不再是一片黑幽幽,反而燈火通明,照耀如晝。
司徒不平站在井口張望,無需照明,亦能清晰看得出來,井底是花崗石地板,似乎只不過兩三丈高。
若非親眼所見,他到這一刻,也還是不願意相信,那白絹上的「井」,指的正是這一口獻祭神龍的神龍井。看見了這花崗石地板,他才終於明白,他親手把其他所有人都送出去了,自己卻留到了最後。
這顯然是一場比賽。最後之人,便是輸家。
這一刻,他只覺方才吞下的那隻蛤蟆,彷彿正在腹腔內放肆起舞,氣得他忍不住渾身顫抖不止。但他不服,滿心不服。帶著憤怒與不忿,他手持長風劍,跳了下去。有寶劍在手,有神功護體,他還抱有一絲希望,說不定還能反敗為勝。
井底下是一間石室,大小與七曜塔閣樓大致相當,裝潢華麗,陳設精美,有床有帳,竟然是一間寢室。室內不見有人,從擺設上看,主人應該是一名男子,但四面牆上,卻都掛了一副仕女圖,畫風恬靜清雅,又透著一股陰柔氣息。倘若司徒不凡也在,多半能看得出來,日作為陽,夜寐為陰,男為陽,女為陰,日為陽,月為陰,這一間寢室,正好對應著七曜中的「月」。
司徒不平沒有在意這些細節,他只看到,在石室一角,竟然還有往下伸延的石階。到了這一步,他早已心無所懼,更不猶豫,走了下樓。
樓下還是一間石室,但風格迥異,開闊空曠,非但沒有多餘的裝潢,更沒有幾件家具擺設。不過司徒不平還是一眼便看出來了,這是一間練功房。四面牆上,密密麻麻掛著許多字畫,字畫上又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小字,還畫了許多人形圖樣。他認得出來,其上記載的,全都是青雲宮藏書閣裡所收藏的高深武學,其中甚至包括了他司徒家的不傳絕學,混沌無極功。
陰為靜藏,陽為施展。夜寢以「收」為用,而練功則以「發」為要,這一間練功房,正合七曜中的「日」。
石室正中,一人盤膝席地而坐,一言不發,似在打坐練功,又似在靜候來人。此人身披斗篷,面目深埋在陰影之中,雖然面對著司徒不平,卻看不清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,只知他身材高大,縱然坐著,也隱隱散發著一股不凡的氣勢。
神秘的斗篷人。
斗篷人看見司徒不平來到身前丈許,終於緩緩扯下蓋頭,露出了面目。燈光下,此人鬚髮灰白,面容剛毅,臉色略顯蒼白,彷彿帶病在身,但一雙眸子卻閃著精光,不怒自威。他雙眉如劍,目光也如劍,任何人被這雙眼神瞪上一眼,都會心裡發毛,不寒而慄。
但司徒不平卻並沒有避開這雙眼神。他瞳孔一收,卻仍鼓著勇氣直視對方,眼神中似隱隱帶著怒火,沉聲說道:「果然是你,宮父!」
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,正是當今青雲宮主,司徒登。
「是為父。」他的聲音冷靜沉穩,近乎無情。
司徒登留書跳崖,所有人都以為他已經死了,司徒不平也不例外。不過此時見到父親仍然健在,他卻沒有顯露出喜悅之情,只冷冷說道:「宮父還活著,宮父沒有死。長風劍在不平手中,長風劍也沒有遺失。」
「沒錯。」
「聖劍不翼而飛,宮父留書跳崖,這一切,都只是一場戲!」
司徒登直認不諱,說道:「一場演給天下人看的戲。不過,你與不凡,卻才是台上主角。」
不知不覺上台演了一場戲,換言之,便是上當受騙了。司徒不平忍著怒氣,問道:「目的何在?」
「為父心中有疑慮。」
「是何疑慮?」
司徒登想了想,說道:「天底下,有兩種人,一種是世間強者,人中龍鳳,可為青雲宮之主,另一種,不可為。你與不凡,孰強孰弱?」
司徒不平哼了一聲,口氣已不再客氣,駁道:「這算什麼疑慮?不平與他,強弱懸殊,顯而易見,毋庸置疑!不平的混沌無極功已練至第七重,此生有望成為自開宮老祖以來,第一位練成第九重之人,不但勝過無數列祖列宗,更勝過宮父!不平若不可為青雲宮主,天底下更有何人可為?」
「還有呢?」
司徒不平更狂妄了,豪邁哼道:「除了武功,不平更有鴻鵠之志!若由不平率領,青雲宮必將大出天下,成就空前絕後之豐功偉業,無論明裡暗裡,都真正做到一統江湖,古往今來,唯我獨尊!」
司徒登輕輕一嘆,搖頭道:「只可惜,武功高強未必便是強者,胸懷壯志也未必便是龍鳳。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。武功可以造福武林,亦可為禍蒼生;野心可以勸人向上,亦可促人成魔。絕世無雙的神功、凌雲吞天的野心,尤為其甚!真正的強者,非不得已不動武;真正的龍鳳,既能翱翔九天,亦能潛淵棲梧;而青雲宮主,更需得能,把江湖看透!」
司徒不平鄙夷哼道:「宮父的意思,是認為不平將成為禍害蒼生的混世魔頭?憑什麼?不平過去數十年來,做錯了什麼?那司徒不凡又做了什麼?憑什麼他便是那造福武林的蓋世英俠?」
他步步進逼質問,但司徒登卻始終保持平靜,只淡淡回道:「為父不敢斷言,所以才說是疑慮。」
司徒不平冷笑譏道:「所以宮父設下迷局,就為了考驗我二人?宮父可知,這毫無意義的迷局,掀起了多少風浪、害死了多少人命?這又算不算是為禍蒼生?」
「算。」司徒登似有歉意,「為父責無旁貸,但為父別無選擇。」
正是因為這一抹歉意,他才沿途救下了無辜被捲入這場風波之人。不過即便如此,「別無選擇」四個字仍不足以解釋他的所作所為,所以他又接著解釋道:「為父大限將至,已沒有多少時間慢慢觀察了,為父必須令你二人馬上分出高下!」
「大限將至?」司徒不平不禁一怔。
「為父為了衝破神功第九重大關,走火入魔,傷了經脈根本,日子已經不多了。」
司徒登神色自若,彷彿事不關己,反而司徒不平卻大為動容。他深知那混沌無極功每次衝關,都有風險,練得越高,風險越大。尤其是先天罡炁不足之人,倘若逆天而為,強行衝關,更會有性命之虞。自開宮祖師以來,歷代司徒家的子弟,從沒有人能攻破第九重大關,其中原因,未必是無人有此能耐,但卻是無人有此勇氣。如司徒不平練至第七重,便已堪稱天下無敵,又何必再冒性命之險更上一重?
二十年前,司徒登以第七重的功力,與七弦劍仙曾有一戰,卻敗於其劍下。他因此才下了決心,最後成功衝破第八重大關。不過功成之後,他卻並沒有找秦藏鋒雪恥,因為他已有必勝的自信。既然必勝,那便無需再戰。有此自信,那他本也沒有任何理由,需要冒險再衝第九重。除非,世上又出現了一個足以勝過他之人。
而這個人,便是司徒不平。
若再懈怠,很快便會被追上了。這不是嫉妒,也不是恐懼,這是習武之人的匠心。尤其是長久以來,都穩坐天下第一之人,更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停滯與懦弱。他被司徒不平激勵了,但代價,卻是性命。這也正是司徒不平動容的原因。世上倘若還有一人能夠明白司徒登當時的心情,那便只能是司徒不平了。不過他卻並沒有因此而內疚,因為倘若換作是他,他也會作同樣的選擇。一旦作了選擇,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,便都是各人造化了,可以怪天,卻怪不得人。
青雲宮裡,尤其是司徒家裡,父子親情不可以常理量度。司徒不平對父親的噩耗並沒有傷感多久,反而胸中怒氣卻只有更盛,他帶著埋怨的口氣,沉聲說道:「即便如此,宮父也不該將青雲宮聖劍交予外人!」
司徒登卻不以為悖,反而說道:「要演好這一場戲,長風劍便必須交給青雲宮以外的人。在此事上,天底下,為父唯一能夠信任的,便只有七弦劍仙秦老弟。」
「宮父與他有交情?」
「非但沒有交情,更有過節。為父當年神功有成,唯一敗績,便是敗在他劍下。世上武林中人,唯有他,敢不對我青雲宮俯首。」
「宮父把聖劍交給敵人?」
「正因他有本事成為青雲宮的敵人,才信得過。只有七弦劍仙,才守得住長風劍,免被任何人所奪。」
「任何人?」
「包括你和不凡二人。」
在這一點上,司徒登信任秦藏鋒,更甚於他自己,因為秦藏鋒與大、小兩位公子,沒有任何交情。提起秦藏鋒,他眼中彷彿又射出了光芒。他當時帶著長風劍,尋到了秦藏鋒。
「司徒兄來戰?」世上能與秦藏鋒一戰之人,已經不多,他心中頗有期待。
「一戰難免,但並非今日。今日,我只來約戰。」司徒登不說原由,只把長風劍留下,說道:「此劍暫托秦老弟保管,他日來取時,便是你我再分高下之時。」
「好。」秦藏鋒沒有考慮多久,便答應了,說道:「此劍既入我手,便再無人可奪,包括司徒兄。」
「除非把秦老弟打敗。」
「除非把我打敗。」
秦藏鋒知道這把劍的份量,也知道這把劍會為他帶來多少麻煩,但他還是把劍收下了。他為的當然不是這把劍,而是這個約定、這個對手。他當時卻沒有想到,這約好的一戰,終究無法實現。
距兩人當年一戰,司徒登武功固然已更上一層樓,但秦藏鋒於琴於劍,造詣亦大有精進。要從秦藏鋒手上奪回長風劍,司徒登雖有把握,但司徒不平卻幾無勝算。這一層,司徒不平有自知之明,所以他愈發惱怒。
「摘星攬月人難尋,飛御長風上青雲。所以這只是一句謊言,甚至是一個陷阱?」
司徒登一笑,莞爾道:「這句話本就沒有任何意思。」
「這句話有意思。」司徒不平反駁道:「這句話的意思,就是要逼不平與司徒不凡相鬥!」
「不鬥,又如何分出高下?」
司徒不平怒氣不減,卻忽感心灰意冷,「這一場比拼,在宮父心中,想必不平已經輸了。」
司徒登不否認:「所有人都離開了,而你卻為了長風劍,滯留至今。若非為父留字提示,你只怕會困死此地。命都沒了,還怎麼贏?」
「他們都還活著?」
「都活著,活得好好的。郭大膛與雲菲語隔世再見,相擁而泣,已雙雙離開山莊,打算回到龍山六月雪塢繼續過日子。鐵丹與秦弦月感情似乎變得很好,帶著小勺子出發,據說是打算去一趟湖北霄山。秦老弟之女,資質不錯,潛力非凡,說不定數年之後,江湖上又會出現一位女劍仙了。至於不凡,」司徒登微微一頓,才繼續說道:「他也活著,並且已然動身,做他該做的事去了。」
司徒不凡不作停留,迫不及待馬上啟程,目的地當然正是雞冠嶺。雞冠嶺上,有遠比長風劍更為要緊的事物,空谷札記。司徒登沒有明言,司徒不平自然也還不知道,他還糾結在眼前的騙局之中,說道:「還有公孫聞道,他當然也還活著。除了那位劍仙前輩,宮父顯然也很信任公孫聞道。你不但演了一幕留書跳崖,更建了這一座見鬼的大千山莊作戲台,派公孫聞道演了一個丑角!」
司徒登點頭坦言道:「聞道的確是為父信得過的心腹,但起初為父並沒有打算把他牽扯進來。你與不凡之間的比拼,後來出現了連為父也始料未及的變化,為父才不得不改變了計劃。若非時間緊迫,為父也不會動用這一座大千山莊。」他一頓,反問道:「你可知這座山莊,本來是什麼地方?」
司徒不平氣道:「只有瘋子,才會在不見天日的地底深處,建一座山莊!」
司徒登一笑,說道:「天底下還有兩種人,一種是活人,一種是死人。死人,便有理由建這一座山莊。有兩座一模一樣的大千山莊,一座『陽院』在地面上,是為父活著時住的;另一座『陰院』在山腹之內,是為父死後的歸宿。這大千山莊,是為父的墓塚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