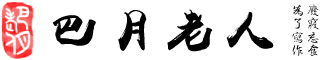苦皆百姓
「這『回頭』二字,有三重意思。」
「哦?」
「這第一重,」肖七指著門外巷子,自嘲道:「客倌請看,這是條窮巷,走到盡頭,不回頭又能如何?」
秦藏鋒點頭同意。
「第二重,」肖七眨著眼望著遠方,繼續道:「不怕見笑,老朽年輕時,是個浪子,後來回頭,才做起這客棧營生,所以就叫『回頭』。」
秦藏鋒一笑,忍不住追問道: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。敢問是何事物,能叫老人家回頭?」
肖七偷偷指了指內堂,低聲笑道:「還不是為了那老婆子咯。」
秦藏鋒會心一笑,心下不由得生出一股暖意。白頭偕老,人生幾何?這一回頭,顯然值得。
肖七笑完,神色一變,變得苦愁,又道:「這第三重呀,客倌,你想必也看見了,這荒城寨,可不比當年嘍,旅人來到此處,最好莫再往前行,該回頭嘍。」
他語重心長,這句話,似乎意有所指。秦藏鋒揚眉奇道:「哦?願聞其詳。」
肖七神色突然變得驚恐,走到巷子裡望了望,確定沒人,才又坐下道:「客倌呀,你願意在老朽這陋室落腳,看得出來,你是個好人。所以老朽便冒險與你說說,免得你在這荒城寨,不慎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。」
「難道這寨子裡,有惡人?」
肖七眨著眼,又遙想當年,說道:「客倌呀,老朽來這荒城寨,開這回頭客棧,也快有二十年光景了。當年這荒城寨,是車水馬龍,老朽的客棧,是門庭若市,遠近商旅,都要到寨子裡來做買賣。直到四年前,」他突然一凜,低聲接著道:「四年前,那蒼狼幫來了,一切便都改變了。」
起初的日子,何長嘯號令嚴明,手下戰士,與居民秋毫無犯。但時間一長,難免鬆懈,一夥殺人如麻的馬賊,又怎可能與部落居民和平共處?餓狗吃屎,毒蛇咬人,天性使然,無法壓制。他們橫行霸道,強搶民女,巧立名目,搜刮民財,巧取豪奪,侵佔民宅,種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,就連大漠蛟王本人,也很快便被那毫無制衡的霸權腐蝕,變得為所欲為,殘暴不仁,苛政雜稅,橫徵暴斂,動輒便胡亂處決居民,看似殺雞儆猴,實則草菅人命。他縱容手下為非作歹,這荒城寨中,不再有王法規矩,而只剩下弱肉強食。人為刀俎,我為魚肉,居民全無申訴之處,有能力的,便偷偷舉家遷走,沒本事的,便只有忍氣吞聲,委曲求全了。只短短數年時間,便把荒城寨本來的繁華,折騰成如今的一片頹敗,百業蕭條。
此時肖七的話,說得委婉,但儘管如此,也還得壓低了嗓子,閃閃爍爍,一臉驚恐,彷彿只要多說了一個字,被蒼狼幫人聽了去,便得人頭落地。無論如何,秦藏鋒卻聽明白了。他微一思忖,也馬上明白了其他好幾件事。門口那極不相稱的牌匾,顯然本來不是為這陋室所準備。這家開在窮巷深處的客棧,也不可能撐得住二十年。肖七的客棧,本來應該正是大街上那一家裝潢華美的鋪子。蒼狼幫人巧取豪奪,搶了鋪子,卻把肖七趕到了這一家陋室之中。正因如此,小勺子才非得要蹲在那巷口,把原該屬於他們家的客人拉回來。
秦藏鋒心中鬱悶,長長嘆了口氣。肖七的遭遇,雖然可憐可嘆,但世上苛政,無處不在,又豈止大漠上一個城寨?即便在中原,甚至是天子腳下,此類百姓悲歌,亦屢見不鮮,他一個琴師,又哪管得了許多?總之一句,天下興,百姓苦,天下亡,百姓苦呀。
他正不知該如何答話,這時七娘正好把酒肉端了出來,他急忙喝了一口,夾起一塊羊肉,塞住了嘴巴。肖七倒似早已習慣了苦日子,不以為意,端詳著桌上秦藏鋒的桐琴,問道:「客倌,是琴師?來荒城寨,謀生?」
秦藏鋒搖了搖頭,答道:「我來此,尋一個人。」
「哦?」肖七問道:「所尋何人?老朽說不定能幫得上忙。」
秦藏鋒側頭邊想邊道:「此人的姓名——多半是個假名,不提也罷。此人的樣貌——多半也經過喬裝。」他自己也忍不住一笑,念頭一轉,又問道:「老人家,最近,可有聽說過什麼奇怪的傳言?比如說,有關於一把劍的傳言?」
肖七一聽,神色一變,搖手不及,說道:「沒有、沒有、沒有。客倌有所不知,大漠蛟王早有諭令,凡寨子居民,皆不得私藏任何兵器,連我家灶房裡的菜刀,都得用鐵鍊鎖上,老朽哪有什麼劍,沒有、沒有,沒聽說過!」
這顯然是何長嘯擔心居民造反,所下達的又一條惡法了。秦藏鋒不禁覺得可笑,但更多的,卻是覺得一陣失望。他從塞內陝西開始,追蹤那人的蹤跡,一路來到此地,那人卻彷彿突然在空氣中消失了一般,再無影蹤。接下來又該往何處尋去?一時之間,他也沒了主意。
正沉思之際,門口突然傳來一陣嘈雜聲,抬頭一看,不禁微微一驚,只見四五個壯漢,凶神惡煞,押著小勺子,來到客棧門前。小勺子正破口大罵,拼命掙扎,但卻被一個連手臂都比他大腿要粗的壯漢,壓制得動彈不得。此時其中一人突然上前一步,指著秦藏鋒叫道:「就是此人!我親眼所見,這兔崽子就是把此人拉走了!人贓並獲,看你如何狡辯!」
肖七嚇得魂飛魄散,急忙趕上前,求道:「錐爺息怒!我家兔崽子不懂事,還請錐爺大人有大量,高抬貴手,放他一馬!」
那為首一人,論體型,倒不是當中最壯碩的一個,只是神情飛揚跋扈,不可一世,叫人望之生厭。他手長腳長,肌肉精實,天靈蓋微微尖凸,像個錐子,取個混號,叫作「癲錐子」,是蒼狼幫內一個小頭目。此時他哼了一聲,冷笑說道:「放他一馬?肖老頭,你家兔崽子不知天高地厚,衝撞我蒼狼幫,也不是頭一回了!老子能放他嗎?」
肖七噗通一聲,跪倒在地,一邊「咚、咚、咚」磕頭,一邊哀求道:「錐爺、錐爺在上,小人給您磕頭了,都怪小人教子無方,今後一定嚴加管教,保證再不敢冒犯錐爺天威,求錐爺格外開恩、格外開恩!」
癲錐子還沒答話,小勺子卻大怒搶著叫道:「爹!你別跪!為何給他們下跪?是他們欺人太甚,我們沒錯,我沒錯!」
肖七恍若未聞,繼續磕頭求饒,額上已滲出血跡。此時七娘聞聲也跑出來了,見此場面,大驚失色,躲在屋裡張望,瑟瑟發抖,也不敢出聲。癲錐子嘿嘿冷笑,悠悠說道:「肖老頭,你派兒子來我門前搶客人,我家少做這一樁生意,你經驗老到,倒說說看,老子是少賺了多少銀子呀?」
肖七忙道:「錐爺的損失,小人賠,小人都賠!錐爺說多少,便是多少!」
癲錐子裝模作樣算了算,嘆道:「罷了、罷了,老子也不欺負你,湊合算個五十兩吧。」秦藏鋒冷眼旁觀,此時聞言,忍不住心中冷笑,他身上碎銀總計不過十餘兩,癲錐子這簡直是漫天要價!不過癲錐子卻還沒說完,他繼續道:「再加上之前的,肖老頭,你前前後後,已欠下三百多兩銀子了!打算什麼時候還呀?」
肖七瞠目結舌,驚道:「三、三百兩?」
癲錐子突然發怒,提腳一踹,把肖七踢得翻了個跟斗,罵道:「怎麼了?想不認帳?爺見你丟了營生,好心好意,把這旺鋪租了給你,一個月才算你三百兩,你不知感恩,還想賴帳?」
肖七跌倒在地,撫著胸口,啞口無言,小勺子破口罵道:「你放屁!當初明明說的是十兩!就這十兩,也還是你強迫我們租的!你這破爛屋子,根本不值兩個銅錢!」
癲錐子笑道:「肖老頭,你家兔崽子是小糊塗,難道你也老糊塗了?老子當初說的,是一天十兩!老子在上一個月圓之夜,把房子租予你,到了明日,又是月圓,正好一個月,三百兩!」
小勺子火冒三丈,氣紅了雙眼,大怒罵道:「你這天殺的強盜!你騙了我家鋪子,還嫌不夠?還想如何?是要把我家榨乾榨絕嗎?別說三百兩,我家三兩都沒有,命倒有三條,有本事你拿去!」
癲錐子聞言,卻正中下懷,喜道:「這可是你說的!還不了債,那便賣身為奴!」
肖七經營客棧多年攢下的財富,早已被癲錐子巧取豪奪搶劫一空,如今是一貧如洗,癲錐子怎會看不出來?但他緊咬不放,把這一家三口逼入絕境,謀的正是這三條人命。在這大漠之上,人命就是奴隸,奴隸可是值錢的商品呀。
這時肖七聞言大驚失色,急忙又磕頭道:「不、不、不!求錐爺網開一面!還!小人還錢便是!錐爺說多少,小人還多少!錐爺是天上神仙,小人是泥裡臭蟲,只求錐爺踩得輕些,多寬容幾天,小人一定把銀子還清!」
小勺子見父親言辭卑賤,怒道:「爹!我說了別跪!」
他怒不可遏,突然不知哪來的力氣,掙脫了束縛,一聲怒吼,抬起了一張長板凳,便朝癲錐子砸了下去。癲錐子還沒來得及反應,身後突然衝出來一人,不擋不架,竟一頭朝板凳撞了上去。只聽「喀嚓!」一聲響,板凳撞得碎裂,那人卻只輕輕摸了摸腦門,哈哈大笑。
秦藏鋒看見此人,也不禁心下動容。此人身材壯碩,比尋常人還要高上一頭,但最奇怪的,卻是整顆頭顱,原來罩上了一頂黑黝黝的鐵頭具,從臉龐到後腦,從頭頂到脖子,除了留下眼、口三個孔洞,竟全包得嚴實。秦藏鋒皺著眉頭,再看細些,心中又一陣駭然,原來那頭罩無縫無鎖,竟是焊死的,也就是說,除非再用烈火焊燒,否則便無法脫下!
這時癲錐子也大笑,說道:「鐵頭!幹得好!」
那鐵頭人,顯然便叫作「鐵頭」了。他大感得意,問道:「錐子哥,這兔崽子不知死活,該怎麼收拾他呢?」
癲錐子臉色一沉,狠聲說道:「敢砸老子?廢了他一雙胳膊!」
鐵頭一怔,提醒道:「胳膊廢了,可不值錢!」
癲錐子道:「老子花得起這銀子,卻丟不起這面子!廢!」
「說得是!」鐵頭領命,伸手一抓,拉住了小勺子手腕,另一手高舉半空,便要朝手肘打下。看他鍋子般大的拳頭,碗口粗細的臂膀,這一打下,莫說骨折脫臼,只怕小勺子半條手臂,要連筋帶肉扯作兩截!
肖七夫婦倆見狀,嚇得魂飛魄散,但鐵頭出手迅速,竟已來不及救人。千鈞一髮之際,「咚!」一聲琴聲響起,鐵頭的拳頭,竟彷彿突然凝結在了半空,再無法動彈分毫。
不止鐵頭,在場所有人,彷彿都被這一聲琴聲震懾,面目駭然,不敢亂動。當然,除了彈琴之人。
彈琴之人,正是秦藏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