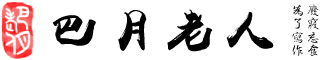圖窮匕現
「凡人,皆有數。」
「此話何意?」
「走路有數,呼吸有數,吃喝拉撒有數,脈搏心跳有數,錢財有數,壽元也有數。數盡了,便沒了。」
「那大師可否算算,在下的錢財之數,還剩多少?」
「你該擔心的,不是錢財之數。」
「難道是壽元?」
「是殺人之數!你殺人之數已盡,若再殺一人,便得一命還一命。」
「如此而已?那也不虧。」
「你不怕死,但很可惜,要還的,卻不是你自己的性命,而是你至愛之人的性命!」
「你這,是威脅,還是算命?」
「老夫秉書直算,從不失算。人算不如天算,天算不如早作打算。但老天若要清算,凡人又怎有勝算?」
——
肖七腦海之中,浮起了當年與周天算的一席話。因這一席話,他作出了選擇,作出了改變一生命運的決定。為了心中至愛之人,他選擇了回頭。如今回想,這一輩子當中,他有許多懊悔與遺憾,但卻絕非是當時的這個選擇。這時,他輕嘆說道:「當年退隱,藏起了『刀』,我心甘情願。但即便不再殺人,也可以有許多種活法。我以為委曲求全,能換來平淡日子。誰能料到,兒子想過的,卻不是平淡日子。」
這句話也說得平淡,但箇中的沉重,又有多少人能領會得到?
七娘感到無比沉重,彷彿窒息。老伴把枷鎖扛在肩上,她卻把老伴扛在心上。兩人沉默良久,七娘才又問道:「那你打算怎麼辦?」
肖七突然起身,走到門外,把門口上那氣派的牌匾拆下,抬了進屋。兩人對視了一眼,有了共識,肖七突然一掌拍出,「喀嚓!」一聲響,牌匾應聲裂作兩段。那牌匾之中,竟有暗格,肖七搖晃牌匾,「吭噌」幾聲,從暗格之內,掉下來三把兵器。
一把長劍,兩把短刀!
兩人盯著兵器,卻沒有動手。七娘再次確認,問道:「真要出手嗎?你不怕那相士之言?」
肖七道:「你與兒子,都是我至愛之人。若應劫的是兒子,他一旦進入蒼狼幫,當了強盜土匪,變得殺人如麻,步我當年後塵,又與死了何異?」正因為他當年曾比何長嘯更嗜殺,所以對小勺子的反應才會如此激烈,他不能眼睜睜看著兒子重蹈覆轍。他又接著道:「若應劫的是你,你怕嗎?」
七娘一笑,笑得慘然,又含著甜蜜,「若是害怕,當年怎會跟你走?」
最害怕的,其實還是肖七。無論何人應劫,他都必須承受。但在這一刻,他還是心懷希望,他說道:「說不定,也並不是非得殺人不可。劫了兒子,我三人遠走高飛,離開大漠便是!」
七娘點頭同意,說道:「無論如何,兒子也有我一份,你若決定出手,我也要出一份力!」
說罷,她撿起了長劍,拔劍出鞘。劍上已有鏽,劍身也暗淡無光,但握在手上,卻還是有一種熟悉的感覺,她平素柔弱的神態,也瞬間消失,變得英氣勃發。她把劍在空中揮舞了幾圈,突然一聲怒吒,朝八仙桌猛力一斬。
聲勢不小,但劍鋒入木兩分後,卻卡住了。她嘆了口氣,問道:「他爹,你的武功,還剩多少成?」
肖七挺著胸膛,答道:「有九成吧。」
七娘撿起兩把短刀,拔出一看,苦笑道:「塵封二十年,刀也鏽了,何況是人?」
肖七想了想,又道:「至少,也有七成吧。」
七娘放下了刀,看著老伴的臉,皺紋縱橫,憂心道:「刀是死的,人卻是活的。人活著,就會變老。」
肖七終於嘆了口氣,「好吧,五成,五成總該是有的。」
——
小勺子邁開腳步,走進了蛟王府中的議事大廳。他的步伐不急不徐,神情也肅穆莊重。他洗了個澡,換了一身新衣,把鬢髮理得齊整,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如此認真面對過一件事。他雙手平捧著蛟龍雕花匣子,上面還蓋了一塊黃絹,以示隆重。
大廳上首,何長嘯大馬金刀地坐在寶座上,夫人薩美、客卿東方九冬侍立兩旁。小勺子走到階下立定,按東方先生之前所教,垂頭朗聲說道:「屬下肖勺子,獻上馬頭禮,請蛟王笑納!禮薄意重,請蛟王萬莫嫌棄!」
何長嘯失笑,眉頭微皺,問東方九冬道:「這扭扭捏捏的儀式,先生教的?」
東方九冬微笑道:「子曰,『道之以德,齊之以禮,有恥且格。』屬下對蛟王敬重,不是壞事。」
何長嘯無奈苦笑。若非東方先生堅持要莊重,薩美此刻本該坐在他懷中才是。他轉頭問小勺子道:「這是何物呀?」
小勺子抬頭答道:「回禀蛟王,這是一個蛟龍雕花匣子,雖然不值錢,卻還算精美,是我家裡最拿得出手之物了。」
「好!」何長嘯走下台階,伸手輕輕撫過黃絹,然後一把掀開,亮出匣子。但一見匣面雕紋,他卻暗暗一驚,神色突變,目光大盛,一把推開了小勺子,奪過了匣子。
眾人大驚,小勺子被蛟王神力推得跌坐在地,更是驚慌錯愕,茫然不已。何長嘯端詳匣子,看清了雕花上的四個篆字,大喜過望,大笑道:「踏破鐵鞋無覓處,得來全不費功夫!」說著把匣子打開,見匣內有一道凹下的劍槽,卻空空如也,有匣無劍,瞬間臉色又變,勃然大怒,朝小勺子怒喝道:「劍呢?長風劍呢?」
小勺子驚恐失措,渾身顫抖,根本無法答話。東方九冬大步上前,驚奇問道:「長風劍?蛟王指的,是青雲宮的長風劍?」
何長嘯沉聲道:「『摘星攬月人難尋,飛御長風上青雲!』天底下,只有一把長風劍!」
薩美也一臉驚疑,緩緩走來,回憶問道:「便是那,大公子吩咐過,即便要把大漠翻個底朝天,也得找出來的長風劍?」
何長嘯點點頭,「萬沒料到,就藏在自家腳下!」
東方九冬沉吟道:「在下聽說過江湖上的傳言,說長風劍失竊,青雲宮亂套,原來是真的?蛟王的意思是,這是長風劍的劍匣?」
何長嘯撫摸著匣面雕紋,篤定說道:「我雖沒見過此劍匣,但當年卻有幸,見過長風劍!匣面上的『青雲』、『長風』四字,與長風劍護手上的四個刻字,如出一轍!匣內劍槽,大小長短、模樣形狀,均與長風劍別無二致!這就是長風劍劍匣,斷不會錯!」他又一轉頭,對小勺子再喝道:「小勺子!這劍匣從何而來?把劍藏在何處?從實招來!」
小勺子總算回過神來了,慌忙跪倒,頭也不敢抬,顫抖著說道:「本、本來就沒有劍!沒有劍!只、只是個空匣子!蛟王曾下令,居民不可私藏任何兵器!小勺子豈敢私藏了劍,又把劍匣獻給蛟王?這木匣子,乃、乃是幾天前一位客人所留下,托客棧代為保管,如、如此而已!小勺子當時就打開看過,裡面確實空無一物!空無一物!」
何長嘯怒道:「你撒謊!那長風劍是何等珍貴之物,豈會有陌生客人,把劍匣交予客棧保管?」
小勺子被蛟王一喝,頓覺彷彿魂飛魄散,腦中一片空白,根本不知該如何辯解,不由得轉頭望著東方九冬,眼中盡是求救之意。不料東方九冬竟突然向他投以嚴厲之色,怒斥道:「小勺子!事關重大,你豈能再為了一己之私,欺瞞蛟王!」他一轉身,向何長嘯抱拳行禮,沉聲說道:「蛟王,在下不敢隱瞞,小勺子曾私下對在下說過,這劍匣真正的來歷!他說,不久前一晚上,入夜之後,他爹肖七,鬼鬼祟祟,與一看不清樣貌的神秘人,在巷子裡相會,竊竊密談。回來之時,懷中便抱著這劍匣!肖七把劍匣在客棧裡藏好,惴惴不安,過不多時,又覺不妥,打開匣子,取出寶劍,獨自出了門,至少隔了個把時辰,方才回來,其時,手上已無寶劍!」他一頓,又搖頭嘆道:「在下當時聽了,以為肖七是不敢冒犯蛟王之令,是以悄悄把劍丟棄銷毀。如今想來,倘若是長風劍,他斷不可能丟棄,定是拿去藏在了某處保險所在!」他突然噗通跪倒,沉痛說道:「蛟王,在下當時,不知事情涉及青雲宮與長風劍,一時大意,鑄成大錯,請蛟王降罪!」
小勺子越聽越是大驚失色,雙眼圓瞪,不敢置信,叫道:「不!東方先生,你為何出言誣賴?我何時對你說過這些?不是這樣的!根本沒有劍,我爹沒有私藏寶劍!沒有!蛟王!我是冤枉的!不是這樣的!」
何長嘯聽得心煩,喝道:「住口!你再撒謊,我斃了你!」
小勺子忙摀住了嘴,忽覺胯下一熱,竟是被嚇得失禁,尿了一褲子。
這時薩美突然冷冷說道:「東方先生,當日引見小勺子,我記得你曾說過,他是你家世交之子。如此說來,那肖七,與你相識?」
東方九冬「坦然」說道:「沒錯。實不相瞞,那肖七正是家父世交。他本是中原武林中人,學過些武功,乃是一名樑上君子,專門幹些偷雞摸狗之事,在下依稀記得,兒時與他曾有數面之緣。聽家父說,他後來被仇家追殺,逃至大漠,從此銷聲匿跡。在下也是來到荒城寨後,才得知此人下落。萬沒料到,事隔多年,他不知悔改,竟重操舊業,更不知死活,打上了長風劍的主意,著實該死!」
何長嘯沉吟片刻,似乎信了,點頭道:「如此說來,此事也不能怪你。起來吧!」
「謝過蛟王不殺之恩!」東方九冬站了起身,又道:「蛟王,在下心忖,這偌大一個荒城寨,肖七要是有心藏劍,只怕不好找。在下有一計,只望可以將功補過,助蛟王尋獲長風劍!」
「說。」
東方九冬沉吟道:「依在下看,肖七此人,雖是個宵小之輩,但對小勺子這個獨子,卻甚是疼愛。」他一抬頭,繼續說道:「蛟王,今晚月圓,正好是行刑夜。且先把小勺子關押,再派人告知肖七,叫他今晚之前,拿劍來贖!如若不然,便在刑場上,取他兒子性命!」
小勺子震驚至極,目瞪口呆,啞口無言。爹爹根本沒有什麼長風劍,如何前來贖人?圖窮匕現,他終於明白,這東方先生,撕下了面具,原來比癲錐子更陰險狠毒百倍,根本是存心血口噴人,根本是要置他一家三口於死地!
事關大公子,何長嘯不敢大意。他來回踱步,皺眉沉思良久,終於有了決定,沉聲下令道:「來人!把犯人小勺子,押到刑場關押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