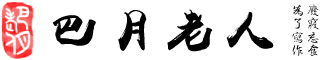鏢銀奇案

清晨,推開窗戶,居高臨下,汀鎮晨景,一覽無遺。
晨陽初昇,天地金黃,鎮子初醒,河面巷間,尚繚繞著縷縷霧氣,但遠處隱約聽得櫓聲輕響,人、舟都已漸漸開始忙碌了起來。
趁著空氣中尚殘留著晨露的氣息,秦藏鋒深吸了一口氣,昨晚一齣戲留在心中的鬱悶一掃而空。昨晚從戲樓出來,天色早已黑了,所幸這一趟,他總算順利找了一家舒適的客棧落腳,舒舒服服休息了一晚。
梳洗過後,下到客棧廳堂,叫了幾盤早點,邊吃邊看街上行人來往,人生百態。
廳堂之中還有不少客人。其中有個和尚,最是引人注目。此人五短身材,但卻體格壯碩,袒露著一雙手臂,肌肉鼓鼓油亮,如石如銅。但最叫人側目的,卻莫過於桌上擺了一盤牛肉,正大口大口吃著,原來是個不守戒律的和尚。也難怪,若只吃素,如何練得出來這一身筋肉?
這時門口進來四五人,為首一人,中等身材,圓臉略胖,看衣著像是不知哪家鋪子的掌櫃,身後幾人身材健壯,似是家丁打手。掌櫃環顧一掃,看見了和尚,臉上一喜,上前抱拳道:「這位大師,想必就是人稱『撞鐘羅漢』的不驚神僧了?」
和尚看了對方一眼,嘴上不停,邊嚼肉邊道:「別神僧鬼僧的,叫和尚便好。你就是汪裕記的馬三德?」
掌櫃點頭坐下,兩人低聲交談。秦藏鋒本不想多管閒事,但聽見「撞鐘羅漢」卻不免留上了神,凝神聽了幾句。兩人說話雖都壓低了嗓子,但自然是逃不過他的耳朵。原來這不驚和尚有些來頭,秦藏鋒也曾聽聞過,據說年少時曾在五台山南山寺出家,負責晨暮敲鐘,經年累月,悟出了一套「撞鐘拳法」。後來離開五台山,在山西、河南一帶闖蕩江湖,頗有些名頭,不知為何,竟來到了江南。秦藏鋒聽他們說了幾句,雖然沒頭沒腦,也大致聽明白了一些。
原來這汪裕記,來頭不小,乃是江南三大鹽商之一。那馬三德是汪裕記在汀鎮的主管,最近似乎為了一些買賣上的糾紛,與汀鎮一家天平鏢局生出了些過節,雙方多次商談,未能解決,漸漸勢成水火。想那鏢局中人,個個習武,汪裕記屢遭壓制,於是經河南澐陽分行的同僚,請到了不驚和尚,前來助陣。
那馬三德說:「我與天平鏢局已然約好,今日正午,在鎮外月老廟前相會,這次無論如何,要他們把事情老實交代清楚!不驚大師來得正是時候,有大師助陣,不怕他們不服軟!」
不驚和尚神情有些倨傲,說道:「事情經過,和尚已經知道了,是那天平鏢局辦事太不地道!既然答應助拳,和尚自會盡力。鏢局的人,不足為懼,倒是不知他們可有請來幫手?」說到此處,他一頓,把聲音壓得更低,繼續問道:「那五渡堂,可會插手?」
馬三德神色一變,四下一望,才答道:「這可不好說。他天平鏢局雖與五渡堂有些交情,但我汪裕記每月對五渡堂也供奉不少!總舵主總得一碗水端平吧?」
不驚和尚哼了一聲,說道:「也罷!他若當真來了,和尚正好會他一會!」
兩人又說了幾句,便一塊離開,神色凝重,看來是去那月老廟赴約了。
秦藏鋒心中大感有趣,沒曾想,來到汀鎮才第二天,正戲這麼快上演了。
江南一帶,乃富庶之地,是天下糧倉之一,官府在此地所徵之糧食、賦稅,要運往京師澐陽,必走水路。官府以外,民間商業發達,各種錢貨往來,也一樣離不開漕運。長江流域地形複雜,河道、碼頭眾多,而掌控這些碼頭、船隻、乃至一切與漕運相關事務的,便是遍布江南各地的漕幫了。漕幫既是江湖行幫,同時也半官半匪。有的受官府雇傭,有的盤踞江段,收取各類「過水費」,有的甚至勾結水賊,一手運糧、一手劫糧。而漕幫之中,勢力最大的,便莫過於五渡堂了。不,應該說,江南一帶各大小漕幫,或直接或間接,無不聽命於五渡堂。五渡堂,就是江南漕幫總堂。再延伸遠些,對民間各種商號而言,漕運都是其命脈。所以如天平鏢局、汪裕記、等,都不得不與五渡堂打好交道。
五渡堂勢力極大,可說掌控了江南一帶所有江湖勢力。不過不驚和尚所忌憚的,卻並不只是五渡堂,更是口中的「他」,指的正是這五渡堂的首領,人稱「總舵主」之人。此人名叫白行舟,有個外號叫「一袖寒江」,據說內力深絕,身懷一門神功「煙波繞寒江」指法,氣勁自指尖射出,一丈內傷敵於無形,極為厲害。
五渡堂勢力遍及江南,白行舟更儼然是江南武林第一人,但五渡堂的大本營、白行舟的日常住所,卻座落在一個看起來祥和安寧的鎮子裡,當然不是別處,正是汀鎮。如若不然,秦藏鋒又怎會來到此處?
當然,單憑「五渡堂總舵主」這一層身份,還不足以叫秦藏鋒為他遠道而來。白行舟還有另一層鮮為人知的身份,才是秦藏鋒感興趣的原因。大公子有三位心腹臂膀,鐵無私、何長嘯相繼身亡,而這「一袖寒江」白行舟,便是第三位。
這時秦藏鋒抬頭看了看天色,離正午還有段時間,施施然又倒了一碗茶,悠悠淺嘗。
——
離汀鎮三里之外,一條小河邊不遠,山林環繞,幽靜清雅,有一座月老廟,自古香火不絕,據說靈驗無比,每逢元宵、七夕,更有遠自百里之外的遊客信眾前來,爭相焚香求緣,在河上放荷花燈,熱鬧自不必說,那在夜裡點點發亮、川流不息的荷花燈流,更是汀鎮一景。只可惜,在兩三年前,此處發生了一樁血案,從此香火驟冷,信眾四散,不過半年,便無以為繼,廟祝悄然離去,神廟自此無人問津,附近一帶也變得人跡罕至。
時至如今,神廟早已荒廢,但廟前河邊一塊空地上,卻是個很適合讓人群在鎮子外聚集的場所。
艷陽高掛,正午時分,空地上此時便分兩個陣營,聚集了上百號人。一邊是汪裕記,以馬三德、不驚和尚為首,帶了四五十個家丁模樣的手下,個個身材健壯,手執長棍;另一邊是天平鏢局,三四十位鏢頭鏢師,個個腰懸單刀,似乎都身懷武功。為首一人約莫五十出頭,頭髮花白,濃眉厚鼻,虎背熊腰,聲音渾厚,乃是總鏢頭韓仲衡,他身旁還有一名鏢頭,年紀稍輕,看樣子未及四十,尖臉黑膚,模樣精幹,名叫羅驍。
雙方一見面便吵了起來,各不相讓。秦藏鋒藏身暗處,聽了半天,才總算釐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。原來約莫兩三個月前,汪裕記委託天平鏢局,運一批鹽貨到澐陽。這本是一趟例行貨運,幾乎每個月便有一趟,兩家合作多年,一直相安無事。這一次押鏢的正是羅驍,如以往一樣,走的也是水路,鹽貨也順利抵達,汪裕記在澐陽的接頭人,名叫劉旺,順利收貨畫押,可是在天平鏢局的人離開以後,打開鹽包,卻才發現貨物不對頭。
要說這貨怎麼不對頭,便又得從頭說起了。這一段隱情,眾人當時不曾說明白,但秦藏鋒見多識廣,稍加臆測,自信也猜了個八九不離十。原來這汪裕記是家鹽號,明面上做的是官鹽買賣,每斤每兩,都有官府鹽引為憑,但暗地裡,卻也買賣私鹽,謀取暴利。這種走私買賣,在鹽業裡不算稀奇,做的也不止汪裕記一家,地方官員多被買通,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。但汪裕記買賣私鹽賺得的銀兩,卻始終是見不得光,不好交由錢莊處理。所以汪裕記把白銀藏在托運的鹽包之中,運到澐陽總行,再作處理。
出事那一趟貨,約有一百包鹽,每包重約五十斤。其中有七十餘包,內裡藏了一百兩白銀,折合約只六斤,對鹽包重量影響不大,一般難以察覺。也就是說,這一趟貨中,其實總計暗藏了七千餘兩銀子。
汪裕記辦事,也算小心。那劉旺領收鹽包時,按馬三德提供的清單,每包秤重,確保無誤。可萬沒料到,回到倉裡,打開鹽包,卻赫然發現,銀子全被換成了同等重量的石頭!
劉旺馬上派人送信到汀鎮,說明情況,馬三德大驚失色,自然便賴上了天平鏢局。那總鏢頭韓仲衡,自幼做腳夫起家,在鏢行經驗老到,可說是德高望重,人們尊稱「衡老鏢」。他三十歲創立天平鏢局,至今二十餘年,生平最看重鏢局聲譽,為人謹慎穩重,數十年來由他親自押運之鏢,從未走失過一次。鏢局內其他鏢師偶有失手,一旦查清是鏢局失責的話,也二話不說,依約賠償,所以鏢局信譽一向極好。這一次出了事,他也不敢馬虎,馬上便找羅驍問責。羅驍一口咬定,押鏢路上沒出任何意外,隨行的其他鏢師,一共另有五人,也全可作證。韓仲衡多方盤問,眾人言之鑿鑿,供詞沒有漏洞,他便採信了,心中已然有數。
這時雙方越吵越僵,馬三德怒道:「無論如何,七千餘兩銀子,你天平鏢局,今日務必得賠!」
羅驍冷哼,反譏道:「空口無憑,你鹽包之內,到底藏沒藏銀子,藏了多少,你說了就算?何不乾脆說是七萬兩、七十萬兩?」
馬三德氣急敗壞,罵道:「衡老鏢!你我兩家合作多年,一向相安無事,這一次分明是你手下手腳不乾淨,你卻一味包庇,你這天平鏢局的招牌還要不要了?」
韓仲衡也動氣道:「馬老闆!我天平鏢局的信譽好不好,你大可去打聽打聽!你委託的鹽包之中,藏了白銀,此事莫說羅驍鏢頭,便連韓某,事前亦不知情,又如何動手腳?再說,要說真有人動了手腳,也不一定就非得是我天平鏢局的人啊!」
他為人穩重,話說得隱晦,但一旁羅驍卻已忍不住,接著道:「正是!說不定,是有人在把銀子藏入鹽包之前,便已換了石頭,也未可知!」
言下之意,是在暗指馬三德夾帶私吞,賊喊捉賊了。馬三德怒不可遏,破口大罵道:「你放屁!看來今日再說更多,也是白搭!不打一場,你等是不會承認了!」
一旁不驚和尚踏前一步,說道:「衡老鏢!你我素未謀面,但和尚敬你是條漢子,再給你一次機會,老實交出贓銀!如若不然,動起手來,怕你面子掛不住!」
韓仲衡心中動怒,沉聲道:「你『撞鐘羅漢』之名,韓某也聽過。我天平鏢局雖只是江南一家小商號,但鏢局上下,也全是鐵骨錚錚的漢子,絕容不得人誣賴冤枉!大師若是想恃武凌人,韓某手上單刀,絕不答應!」
不驚和尚摩拳擦掌,哼道:「敬酒不吃,吃罰酒!和尚便來會會你手上單刀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