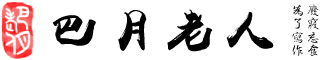琴心劍意
夜色漸深,華燈初上,河面上一條輕舟靜靜滑過水波。舟身細長,船頭掛著一盞淡黃燈籠,燈影搖曳。
兩岸屋舍臨水而建,樓閣亭台錯落有致,門窗戶前挑掛起燈籠,燈火倒映河中,宛如天星沉入水底。
秦藏鋒盤膝坐在船頭,一邊望著兩岸緩緩後退的夜景,一邊淺嚐手中一壺美酒。
不久前,輕舟經過戲樓茶館,尚聞人聲鼎沸,但漸漸地,人潮變得稀落,四下也變得一片寂靜。
秦藏鋒突然一笑,放下酒壺,從背上取下桐琴,平放膝上,還尚未撥弦,忽聞船尾「噗通」一聲,卻是艄公竟突然跳了下水,瞬間沒了蹤影。
秦藏鋒面不改色,彷彿事不關己,開始彈琴。琴聲悠揚,劃破寂靜,但曲調肅殺,節奏緊湊,每一聲琴音,都像是長劍揮斬,餘音迴盪,宛如劍光留影,彈奏的正是一首《十面埋伏》。
琴聲不斷,殺氣四溢,這條幽靜的河道,彷彿變成了戰場。小船順流緩行,前方不遠,一座拱橋橫跨河上,橋上正中,一人寬袖長袍,負手而立,神態自若,似在看景,又似在等人,彷彿絲毫不受琴聲影響。
船飄到橋前,橋上人動了。他凝神運氣,一手大袖緩緩揮動,似帶動了一股氣流,拱橋下方河水突然湧起陣陣輕波,緩緩散開,小船被水波輕推,漸漸停下。
一曲正好彈罷,四下恢復幽靜,秦藏鋒雙手停在琴弦上,緩緩抬頭。
橋上人自然便是白行舟了。對五渡堂來說,要在汀鎮找一個人,並不難,半天足矣。他開口說道:「恭候多時。」
秦藏鋒輕輕一笑,「總舵主等我,莫非是,想聽我彈琴?」
白行舟道:「這一首《十面埋伏》,氣氛激烈,殺氣躍然,聽之,彷彿親見項羽決戰劉邦,不同凡響,的確值得一聽。」
江湖上懂音律之人不多,但白行舟自幼修文習武,對樂理正好也略有涉獵。秦藏鋒又遇知音,不由得一喜,問道:「那你我之間,誰是項羽?誰是劉邦?」
白行舟臉上卻不見息怒,淡淡答道:「白某既不想當項羽,也不想當劉邦。」
「那總舵主想要什麼?」
「要足下的琴!」
秦藏鋒笑了,微笑問道:「一具凡桐,總舵主要之何用?」
白行舟臉色一沉,答道:「琴是凡桐,但琴中有寶!」
秦藏鋒長聲一嘆,覺得可惜,問道:「只要琴,不要命?」
白行舟答得乾脆:「先要琴,再要命!」
「太貪心了。」秦藏鋒搖頭笑道:「要琴要命,總舵主只能選其一。」他神色突然一變,沉聲接著道:「我的琴,總舵主的命!」
白行舟冷冷一笑,說道:「口氣不小,且看手下真章!」
話音落地,他雙手大袖一揮,人彷彿化作了一道白霧,朝秦藏鋒飄了過來。他的身法看似輕飄飄地,毫無威勢,但其實卻極為迅速,只一眨眼間,便已來到五尺之內。他寬袖飛舞,亂人耳目,雙手藏在袖中,毫無預兆,突然出招,一指擊出,指勁透袖而出,凌厲無匹,一丈之內,削金斷鐵。不過就在他出招的同一時間,秦藏鋒也撥了一弦。「咚!」一聲沉沉響起,這一聲貫了內力,殺氣凜然,冷冽森寒,彷彿就像一把利劍,直擊人心房,忽又化作一掌,在人心上緊緊一握,彷彿能叫人心跳暫時停頓。
這一手絕技,不久前在回頭客棧,他曾施展過,當時隨性而彈,並未用力,已令癲錐子、鐵頭等人動彈不得。此時全力施為,威力不可同日而語,縱然是高手如白行舟,毫無防備心之下,亦難倖免,但覺心頭突然一震,腦海彷彿有一剎那,變得一片空白。但比這一撥弦更高明的,卻是那撥弦的時機,不遲不早,毫釐不差,彷彿白行舟一絲不掛,內息運行、血脈流淌,全被他一覽無遺。
這精準的時機、懾人的琴聲,就令白行舟那一指氣勁,偏了兩分。差之毫釐,失之千里,「嘩啦!」一聲巨響,小船旁三尺外,河水突然一爆,激起數丈的水花,直衝上天。
水花方起,秦藏鋒人也躍起。他一手抱琴,一手伸出兩指,迎上白行舟,「咻、咻、咻!」瞬間劃了三招。白行舟瞳孔驟張,心下大驚,暗罵了一聲:「該死,輕敵了!」急忙撤招,兩袖流轉,護住了全身。這一招名叫「寒波千疊」,大袖暗藏內勁,化力卸勁,是毫無破綻的守勢,一旦使出,便是刀劍利器,亦難傷他分毫。
同一時間,他見對方以兩指出招,心中又一驚:「此人用的也是指法?」但當秦藏鋒招式落下,他馬上又看明白了,對方兩指,不是指,而是劍!沒有劍刃,卻有劍氣!而這一道劍氣,卻竟比尋常刀劍,更為鋒銳!
秦藏鋒的劍法,乃年輕時彈琴有悟所創,取名「琴心劍意」,融合了樂理與武學,出劍如彈琴,講究的是韻律有致,和諧自然,暗合天道,天人合一。他憑意出劍,沒有招式,只有五種劍勢,暗合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。五音相混,能演奏萬千樂曲,五勢相交,便能變化萬千劍招。他三十歲時劍法大成,此後十餘年,練的已不是劍法,而是劍心。正因心中有劍,所以即便是以兩指出招,也能有劍氣!
兩人在半空中,一瞬間交手十餘招,又驟然分開。秦藏鋒落回到船頭站好,白行舟空中一個筋斗,也一樣回到了拱橋上。他方才穩住身子,突然夜風一吹,手臂一涼,身上兩片大袖,竟裂成了碎片,隨風輕輕飄起,漫天紛飛,宛如深秋落葉。他大為震動,眼前「琴師」的武功之高,實屬生平僅見!片刻前還自責大意輕敵,此時方知,實力懸殊,勝負根本與此無關!他又驚又怒,忍不住抬頭喝問道:「足下到底何人?」
秦藏鋒淡淡回道:「總舵主已作出了選擇,現在再問,已太遲了!」
一句說完,又已出手。他縱身而起,一劍刺出,直指白行舟眉心。這一劍平平刺出,看似樸實無華,但劍招之下,卻暗藏一股悲涼劍意,招未到,意先行,這股劍意與他的琴音有異曲同工之妙,彷彿能直擊人心,叫人無法抵抗。白行舟心中莫名生出一股悲涼哀傷,沉浸其中,竟忘了閃躲。這種劍意絕不是迷惑人心的邪功,而是如樂曲一般,是一種能感染人心的天道!
白行舟沉浸在劍意之中,這一劍彷彿來得極慢,但在外人看來,這一劍其實卻迅疾如風,只一眨眼間,便已逼近眉心三寸。
千鈞一髮之際,半空中突然傳來一陣口哨聲,吹奏起一首輕快的曲子。哨聲不響,但四下寂靜,卻清晰可聞。白行舟為了伏擊秦藏鋒,早已暗中命人把附近居民調走,那這把哨聲從何而來?更叫秦藏鋒驚詫的,卻是這把哨聲與曲子,音調悠揚,節奏輕快,幾分輕佻,幾分俏皮,如晨初鳥歌,竟意外地悅耳,令人聽了,身心愉快,與他此刻劍意相呼應,是截然相反的一種意境。
這把突如其來的哨聲,雖不足以打破秦藏鋒的劍意,但秦藏鋒的劍卻還是在白行舟眉心前停了下來,劍意消散,劍也化回了雙指。白行舟這才醒了過來,嚇出一身冷汗,正想出手反擊,秦藏鋒卻已撇下了他不管,轉身腳一蹬,疾射而去。
比起殺人,秦藏鋒此刻對這哨聲主人更感興趣。此人能感悟到劍意,更能精準吹奏出與劍意相剋的曲子,絕非泛泛之輩,肯定比白行舟有趣多了。
哨聲已停,他憑著記憶循聲追去,果然發現了一名蒙面黑衣人。黑衣人伏身在一座樓閣屋脊之上,顯然一直在窺視他與白行舟之戰。見他追來,黑衣人不慌不忙,站了起身,朝他看了一眼,轉身便走。
就這一眼,秦藏鋒已然看清。這黑衣人身形苗條,是個女子,只露出一雙眸子,眉目秀麗,透出一股英氣,很是熟悉,不久以前,不但打過照面,還同桌看了一齣戲。「原來是她!」秦藏鋒心中一動,繼續追上。
黑衣人施展起輕功,躥房越脊,飛簷走壁,不多時,已奔出了汀鎮,來到郊外。不遠處,一片荒野之間,有一所古樸的大房子,黑衣人直奔到圍牆大門前,突然放慢了腳步,緩緩推開大門,走了進去,卻不關門,彷彿是在等著秦藏鋒。
秦藏鋒冷冷一笑,他藝高人膽大,毫不遲疑,跟了進去。
大門內,是一所院子。黑衣人站在屋前,背著大門,負手而立,待他來到身後,才銀鈴般輕輕一笑,突然猛地一轉身,奇事便發生了。她明明穿著一身緊身黑衣,但在轉身那一瞬間,卻突然變了,變成了大袖短襖、百褶長裙,與當日在聽潮台的穿著一樣,正是那弄紅塵戲班的紅絮姑娘。
饒是秦藏鋒見識廣博,眼力犀利,也看不出她這一手神技,是如何辦到,若非親眼所見,斷不敢置信。
紅絮看他吃驚的模樣,大感有趣,眉宇之間多了一股少女的淘氣,笑著說道:「秦先生大駕光臨,敝班蓬蓽生輝呀。」
秦藏鋒此刻,心中有許多疑問,都比紅絮表演的戲法更重要,但他想了片刻,最後還是一聲輕嘆,說道:「據說在四川一帶,有一種變臉戲法,能瞬間變換面具;我有一年在澐陽,也曾見過一位西域藝人,能在彈指之間易服換裝。但要做到如紅絮姑娘這般,無遮無掩,瞬間換裝,他們都遠遠不及。神乎其技,秦某開眼界了,佩服。」
紅絮掩嘴一笑,說道:「先生學琴,也練劍,應該很能明白其中道理。凡事只要練到極致,自然能人所不能。戲法也是台上一種表演,敝班偶有涉獵,紅絮獻醜了。」
琴、劍之理,既能相通,戲法又為何不能?秦藏鋒點頭同意,口氣一變,又說道:「不過看來,貴班所涉獵的,可不止戲曲戲法。」
紅絮問道:「先生所指,是我方才一身黑衣?」
秦藏鋒單刀直入,問道:「姑娘與白行舟,有何關係?」
紅絮坦然答道:「非親非故,無怨無仇。」
秦藏鋒又問:「姑娘當時救他,口哨所吹,是何曲子?」
紅絮卻臉一紅,靦腆答道:「一時情急,臨時亂吹,叫先生見笑了。」
「臨時亂吹?」
紅絮坦然道:「確是如此。先生的劍法太快,紅絮無力阻攔,心中一急,不知不覺,便吹起了口哨。先生若要再追問,紅絮也著實答不上來了。」
秦藏鋒察顏觀色,看紅絮不似說謊,心中暗暗吃驚,再問道:「既然非親非故,為何要救他?」
紅絮微微一笑,卻不作答,抬頭看看星辰,說道:「夜已深,先生想必也累了,何不在此過上一夜?」
秦藏鋒看了看房子,幾扇窗戶內隱約有燈火閃爍,顯然有人,問道:「這是什麼地方?」
紅絮答道:「這所房子,是敝班來到汀鎮,臨時租下。如今,正是敝班沒上台時,落腳之處。」
秦藏鋒一笑,說道:「姑娘說過,貴班全是女眷,留我過夜,不怕人言可畏?」
紅絮笑道:「若怕人言,誰還入梨園?房子大得很,客房有的是。更何況,堂堂『七弦劍仙』,敝班上下,都信得過。」
秦藏鋒心中一凜,原來紅絮已看出了他的身份。看紅絮不過二十出頭,他當年隱退江湖之時,紅絮最多也還在襁褓之中,小小年紀,竟能說得出他的名號,可知此人來歷,必非比尋常,這弄紅塵戲班,更說不定藏了什麼秘密。
他還在思忖,紅絮又已說道:「紅絮知道,先生心中,有許多疑問。不急,待天明,我自會給先生一個交代。」
隨一位來歷不明之人,與一群神秘組織的成員,到一處陌生房子之中,過上一夜?有趣。
「前面帶路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