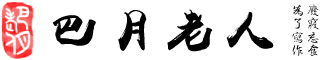青衣正旦
「如何?」紅絮眼神中帶著興奮與期待,問道:「先生覺得,這《破妝台記》第一折,可還過得去?紅絮覺得,畫骨大娘的筆下妝容、彩袖姐的念唱做打,兩人技藝彷彿又精進了。」
秦藏鋒板著臉,冷冷問道:「你們演這一齣戲,到底目的何在?」
紅絮眨了眨眼,帶著淘氣問道:「先生猜猜?」
秦藏鋒哼道:「陸懷章與沈棠,我見過。兩人情投意合,更有婚約在身。你等此舉,是在棒打鴛鴦!」
紅絮道:「他倆不但有婚約,而且兩家還已商定,半年之後,便要成親完婚,喜結連理。」
秦藏鋒不想多管閒事,但心頭卻還是忍不住燃起一絲怒火,冷笑道:「你弄紅塵是收了誰家銀子,幹此缺德之事?」
想當時在荒城寨,他眼睜睜看著趙切掉進東方九冬設下的陷阱,最後家破人亡,也不曾動氣過,但這區區汀鎮一對小情侶,卻似乎觸動了他某處深埋心底的記憶,竟為兩人感到一絲心疼。紅絮看在眼裡,忍不住掩嘴一笑道:「原來先生也是個善感之人。」
她一頓,又抬頭看天,悠悠說道:「那沈棠妹妹,紅絮也認識。她特別愛看戲,常到戲樓捧場。有一次,她對我說起婚事,心中忐忑,擔心她的『懷章哥哥』,心志不堅,只怕成親之後,會喜新厭舊,始亂終棄。她還說,倘若有個法子,能讓她看清『懷章哥哥』的真心,便太好了。」
少女婚前,心情忐忑,既害怕,又憧憬,這種心情秦藏鋒能夠理解,他很多年前,也曾見過不少,但他卻還是不明白紅絮的意思。
紅絮繼續解釋道:「先生說對了一半。敝班演這一齣戲,的確是受人所託,但卻不曾收取分文。而委託之人,便正是沈棠妹妹。」
秦藏鋒皺眉道:「你的意思,這一齣戲,是為了一試陸懷章的真心?」
紅絮收起了淘氣,正色道:「不止陸懷章。人世間,男子可以始亂終棄,女子亦有虛情假意。敝班一視同仁,沈棠妹妹,也一樣得經過考驗,才知心意是否堅定。」
秦藏鋒思忖了片刻,彷彿明白了,冷笑道:「如此說來,沈棠委託貴班演這一齣戲,只怕是連沈棠自己,也不知情吧?」
紅絮直認不諱:「她倘若知情,又如何經歷考驗?她提出了疑慮,敝班觀察了兩人,認為值得一試,所以便寫了《破妝台記》。」
秦藏鋒哼道:「那貴班此舉,就是多管閒事!」
紅絮想了想,問道:「紅絮請教先生,何為俠?」
很多年前,秦藏鋒也自詡為俠。他不假思索,答道:「路見不平,拔刀相助,是為俠。」
「說得好!」紅絮神色變得肅穆,說道:「世間有俠客,伸張正義,好人免遭欺侮,惡人難逃懲治。但情場中的惡徒,卻恣意橫行,逍遙法外。我弄紅塵,願當這情場中的俠客,不問忠奸善惡,但求一片真心。這,就是我弄紅塵的使命!」
江湖上無奇不有,秦藏鋒也見多了,但這標新立異的使命、行事詭異的組織,卻也還是叫他大開眼界。弄紅塵自比情場俠客,這番說法,似是而非,卻又不無道理,叫人一時不知如何反駁。或許,俠客以武揚道,私行正義,在外人看來,也一樣不可理喻?秦藏鋒不由得陷入了沉思,過了良久,才又質疑道:「退不退婚,似乎全看陸允中的決定,陸懷章與沈棠,根本無法左右。你又如何考驗他們?」
紅絮神秘一笑,說道:「先生別急。這一齣戲,才演了一折,接下來,自有更精彩的劇情。但紅絮卻不想過早透露,免得壞了先生看戲的興致。」
秦藏鋒又覺無法反駁,只好輕嘆道:「我來汀鎮想看的,不是這齣《破妝台記》。」
紅絮點頭,「紅絮知道,先生想看的,是總舵主白行舟主演的戲。」
秦藏鋒不耐煩了,直接再問:「你昨夜為何要救白行舟?」
紅絮微笑道:「紅絮讓先生看《破妝台記》,只是為了向先生解釋弄紅塵的使命。先生明白了這一層,再看白行舟的戲,便更能有所體悟了。」
秦藏鋒心中一動,雙眼突然一亮,追問道:「你的意思,白行舟也成為了貴班想要考驗的目標?」
「先生猜得沒錯!」紅絮坦言答道:「所以紅絮希望先生在殺白行舟之前,先看一看這一齣新戲《末路客》。況且,」她俏皮一笑,繼續道:「先生昨晚,已親身參演了第一折,理應對接下來的劇情,很感興趣才是。」
「你的意思,」秦藏鋒目光閃動,沉聲說道:「昨夜白行舟埋伏刺殺我,是一場戲?你寫的戲?」
紅絮忙搖手笑道:「我弄紅塵再神通廣大,也不可能請到總舵主來當這武生。這不是紅絮撰寫的情節,紅絮也只是個觀眾。但這一場武戲,的確就是《末路客》第一折。而且,重點不是刺殺,而是刺殺不遂,任務失敗!」
秦藏鋒深吸了一口氣,不得不承認,他已漸漸被紅絮勾起對這一齣《末路客》的興趣。他問道:「那第二折,何時上演?」
紅絮抬頭看了看天色,語帶神秘,繼續道:「我估計,先生也不必等太久,說不定,今晚便要上演了。」她一頓,又道:「不過,在看第二折之前,紅絮還得先為先生引見一位角色。」
「什麼角色?」
「一位青衣正旦!」
——
汀鎮一隅,有一家小巧別致的繡坊,名喚「翠雲閣」。白牆黛瓦,臨水而建,門前栽著兩株丁香,香氣清雅,掩映著一道細緻的雕花木門。
翠雲閣是家小商號,名頭不響,但繡坊的針線手藝卻著實不錯,有不少大商號暗裡都把客人訂製的繡品交給他們代工,翠雲閣也從沒讓這些大主顧失望過。所以翠雲閣門口客人雖不多,但坊裡幾位繡娘卻總有幹不完的活。
幾位繡娘的手藝固然好,但最重要的卻還是翠雲閣的主人。這主人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,只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平凡女子,名叫雲菲語。
雲菲語自己也是一位繡娘,而且手藝出眾,下針細膩婉轉,善繡山水、花鳥,尤其擅長詩句入畫。繡坊中大廳掛著一幅《月下紅梅》,梅枝傲骨,詩句清冷,正是她的得意之作。她從八歲開始便在繡坊幹活,從一個小小的掌針姑娘幹起,勤學苦練多年,才有如今的技藝。她如今雖是繡坊主人,性子卻極好,從不擺主子氣,而且事必躬親,常常親自下手,與繡娘們一同刺繡,一邊細聲講些故事,一邊落針如水。對坊裡其他繡娘的作品,她也必細心過目,嚴謹把關,滿意之後,才敢交貨。
她生活簡樸,那繡坊的後院,便是她的住處。她每日辰時便早早起身,清水洗面,梳一個簡單的雙鬟髻,穿一襲淺青布衣,腰間束一條杏黃色繡腰帶,不華麗,卻整潔雅緻。在繡坊辛勤一天,天黑便又回到後院,作息簡單有序。
曾有人勸她,坊裡的活既然已做不過來,便該擴展繡坊,多僱幾位繡娘,把商號做大。名頭響了,少幹些薄利的代工,多接待些富家客人,銀子自然賺得更多。但她卻不願。她對目前安定平凡的日子,滿意知足,相反,她最怕名聲太響,招惹是非。
但說她平凡,卻又不平凡。她雖幾乎足不出戶,但街坊鄰里都知道,那雲菲語,可是個少見的美人。她的美貌,不在嬌豔,而來自於一股純樸之氣。她眉眼清秀如畫,神態純樸無邪,眼神澄澈如湖水,似能一眼望見心底。她不施脂粉,卻自有一股淡淡的香氣,彷彿是夏日陽光下的草木清香。
鎮上不少世家公子、富商才俊,聽聞她模樣出眾、性情溫婉,又正值花信之年,紛紛藉故造訪,一睹芳顏後,都為之傾倒。他們送花寫詩,熱烈追求,遣來媒婆串門,百般求親,甚至曾有財大氣粗的豪商擺起十里紅妝,要納她為妾,卻全都被她婉拒了。
坊裡有相熟的繡娘,紛紛勸她,女大當嫁,切莫眼高於頂,誤了終身。她總是含羞敷衍,只說心中有數。旁人不知,其實她這副身子,早已有主。那個「他」,家財萬貫、有權有勢,只可惜,也早有家室。兩人之間的關係,見不得光,雲菲語為了保全他的名聲,心甘情願嚥下苦水,默默承受風言風語。
雲菲語記憶猶新,四年前偶然相遇,他便直截了當,袒露愛意,眼中流露出對她身子的熾熱渴望。他是個成熟乾脆的人,無暇曖昧與猜測。當時雲菲語還只是個掌針下人,懾於他的權勢,全然不知如何拒絕,半推半就,便屈從了他。萬幸他是個憐香惜玉的男人,從此對她不離不棄,愛護有加。她知道,他利用財富與權勢,不動聲色,多次暗中替她解決了不少麻煩。有一次,她在坊裡幹活,因一件小誤會,繡坊主人對她無理責備。他得知後,一怒之下,索性買下了這家繡坊,轉送予她,依她之名,改名「翠雲閣」,讓她自當主人,免得再受人氣。當時的情景,她歷歷在目,至今依舊滿心感動。
她出身清貧,父母早亡,自小寄人籬下,生活艱苦,受盡冷言冷語。她當時每日起早摸黑,刺繡換食,指尖常被針頭刺破,血跡與絲線混在一塊,日復一日地掙扎求存,看不見未來有任何出路。直到這個男人在她生命中出現,黑暗中才有了曙光。這個男人起初把她擁入懷中,雖然半帶脅迫,但她後來卻漸漸發現,他的胸膛溫暖堅實,足可依靠。相處四年,日久生情,到了如今,她不但已習慣了當他秘密情婦的角色,更漸漸對兩人相見的日子,心生期待。
這個男人的行蹤難以捉摸,但隔三岔五,必會來坊裡看她。不過兩人之事不能聲張,他每次出現,都悄無聲息。他會在進入後院的月門上,掛上一條草青色絲帶,這就表示今天晚上,他會在後院等她。這一天,午飯過後,她經過月門,如常張望,驚喜又見到了青絲帶。她有些激動,急忙趕回到坊裡,埋頭趕製一條白絹繡帕。
不久以前,他的一條繡帕不慎掉進了火盆中,燒毀了大半,他很是傷心。雲菲語不知道這條手帕的來歷,卻只知他貼身攜帶,向來很是珍惜。她暗暗記下手帕上的繡圖與詩句,打算為他新繡一條。她親手打版、畫稿、鋪棉、刺繡,用針多日,已完成大半,還有半天時間,她得趕緊勾勒收尾、開面結裡。她一邊下針,一邊想著今夜相見,送上新帕,他一定會很歡喜。
日漸西斜,轉眼天黑,坊裡繡娘們都已離開回家。雲菲語關門打烊,將剛完成的繡帕細心折好,裝入一方錦盒,藏入衣襟。她輕步穿過月門,走向後院,心裡柔情萬千,臉上也不自覺流露出了一抹甜蜜笑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