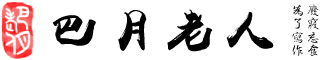紅燈私語

苦酒滿碗,白行舟一飲而盡。
酒入愁腸愁更愁,白行舟胸中鬱悶,不覺有絲毫緩解。他想不明白,堂堂五渡堂總舵主,江南武林第一人,怎會落魄至此?
夜色微涼,月華如水,院子中一棵桃樹下,掛了一盞紅燈籠,隨風搖曳。樹下一張石桌,白行舟自斟自飲。江風送來了丁香的香氣,其中又夾雜著一股淡淡如青草沐浴在陽光下的氣息。
一隻纖纖玉手伸了過來,在他胸口輕輕撫慰,白行舟眼中總算露出了一絲溫柔。世上倘若還有一個人,能消除他心中的苦悶,那便一定是這玉手的主人了。他握住玉手,輕輕一拉,女子「嚶」地一聲,跌進了他懷中。
正是雲菲語。她每次出現在眼前,白行舟都有一種晨霧初散,清新涼快的感覺。
雲菲語的「他」,正是白行舟。像白行舟這樣的男人,即便有七八個情婦,也不會讓人感到意外。讓人意外的是,他就只有雲菲語一個情婦,彷彿對這個女人,的確情有獨鍾。
此時雲菲語手指輕揉情郎皺成一團的眉頭,心疼問道:「是誰又惹舟郎煩心了?」
她語聲輕柔,帶著江南女子獨有的溫婉。白行舟腦海湧起一張惹人憎惡的面孔,哼道:「還能有誰,當然是那潑婦婆娘了!」
「夫人?」雲菲語略感愧疚,輕嘆道:「終究是一場夫妻……」
「什麼夫妻!」白行舟忍不住打斷,憤憤不平說道:「那潑婦只不過是大公子派來我身邊的,盯著我一舉一動的探子罷了!」
雲菲語柔聲勸道:「夫妻亦假亦真,這麼多年,都忍耐過去了。菲語沒見過那大公子,但記得舟郎說過,大公子得罪不得。」她突然神秘一笑,從懷中取出一個錦盒,繼續說道:「舟郎若是實在心煩,菲語有件心意,或正好可為舟郎排憂。舟郎你看,這是什麼?」
白行舟打開錦盒,取出一看,原來是一條白絹繡帕。帕上繡著一枝紅豆藤,蜿蜒而上,點點紅豆如淚珠,纏繞著淡青色的花紋,溫柔而纏綿,一旁還有一首詩:「紅豆生南國,春來發幾枝。願君多采擷,此物最相思。」
他看見繡帕,平日在人前鋼鐵般的心腸不禁頓時變得軟綿。他有一條一模一樣的手帕,對他是極為重要的事物。不久前燒毀了,正感惋惜,不料雲菲語竟花費了心思,為他重新繡製了一條。他心中感動,但美人柔情,他卻消受有愧,不由得心中一聲輕嘆。
雲菲語並不知道,那燒毀的繡帕,也是很多年前,一位女子所贈。那女子當年,也是汀鎮裡一位繡娘。當時他與那女子兩情相悅,本承諾一生廝守,但他年少氣盛,血氣方剛,卻決定要離開汀鎮,去闖蕩江湖。臨別,女子繡贈絹帕,說道:「願你孤身在外,見絹帕如見我,勿忘我對你,相思如豆。」
他本承諾,半年即回。不料一去五年,而且回到汀鎮之時,業已娶了夫人姚俐。他本以為女子也早已嫁人,卻不料女子竟原來一直守身如玉,苦苦等他。驚聞噩耗,女子一病不起,最後投河自盡,屍骨無蹤。
他當時悲痛欲絕,直到如今,這也還是他一生難以釋懷之痛。所以當他四年前見到雲菲語時,才會難抑心中激動。雲菲語不但一樣是個繡娘,而且眉宇神態,氣質言行,都與那徘徊在心中的女子有幾分相像。他一時失控,強行佔有了她,事後心中略感愧疚,暗中決定,要好好待她,決不重蹈覆轍,再負佳人。
數年相處,雲菲語溫柔體貼,處處順從,安分守己,知足不奢,與青蓮書院中那位夫人姚俐相比,判若雲泥。日久生情,他從把雲菲語看成是當年情人的替代,到把這段情緣看作是自己當年背叛的救贖,再到對雲菲語漸漸生出真情,如今再看這條手帕,心中不由得一陣唏噓。他感慨良久,輕嘆說道:「菲語,你跟我多年,卻始終沒有名分,你我只能在夜裡相會,見不得陽光,委屈你了。」
「不,」雲菲語搖頭道:「菲語不覺委屈,也不需要名分。菲語不要舟郎為了我,而與大公子發生不快!」
若要爭名分,難免與正室夫人發生衝突,而白行舟也說了,姚俐本就是大公子的人。白行舟眼神突然一變,變得堅定而銳利,冷冷說道:「但這一次,只怕是免不了了!」
雲菲語微微一驚,「那是為何?」
白行舟把酒滿上,又一飲而盡,緊握拳頭,忿然說道:「大公子交代的任務,我失手了。」
雲菲語道:「人有錯手,馬有失蹄。亡羊補牢,未為晚也。菲語知道舟郎本事高強,再接再厲,定能成功!」
白行舟想起昨晚命懸一線,心有餘悸,搖頭苦笑道:「你不懂。那人的劍法,太可怕了,我遠不是他的對手!」
雲菲語深為情郎抱不平,說道:「既然如此,那大公子也不能怪罪於舟郎啊!」
白行舟還是搖頭,說道:「再加上,那潑婦在追問鏢局的案子,似乎對我也已起了疑心!」
昨晚刺殺秦藏鋒的行動,可不是一樁尋常的任務。事關長風劍,牽連極大。白行舟昨晚敗得狼狽,堂堂「一袖寒江」兩袖盡碎,光著膀子回到青蓮書院,姚俐見了,冷笑連連,不但無情奚落,說盡了難聽的話,更恫言大公子得知後,必要治他一個辦事不力之罪!白行舟知道,這並非虛言。自長風劍不翼而飛、老宮主留書跳崖以來,快半年了,大公子無一日不追問搜尋聖劍下落的進展,可見對此事之重視。加上近來鐵無私、何長嘯相繼身亡,大公子的心情已是極差。好不容易有了長風劍的線索,若非他太過自信,事前沒有打聽清楚那琴師的來歷,便貿然出手,也不致有此慘敗。如今打草驚蛇,即便再想召集青雲宮高手前來圍捕,也已是萬難了。
白夫人姚俐與白行舟的關係,也說來話長。當年白行舟離開汀鎮,闖蕩江湖,憑卓越的身手,很快便引起了大公子的注目。大公子看得起他,與他相交,為他打點關係,拉攏各大漕幫,甚至傳授絕世武功,讓他一躍成為五渡堂總舵主,為青雲宮管理江南武林,手段與拉攏何長嘯如出一轍。
但大公子卻也看得出來,白行舟與何長嘯不一樣,他的行事作風,未必事事都能與青雲宮的利益保持一致。所以當時,就為他物色了一位妻子,姚俐。姚俐的出身,與青雲宮有千絲萬縷的關係,簡而言之,可說是大公子的遠房表妹,為了自己,也為了家族,她對青雲宮、對大公子死心塌地,絕不敢有二心。把姚俐嫁給白行舟,有聯姻之意,同時如白行舟所說,亦有監視督察之用。
這一層用意,白行舟自然曉得,他當時也還記得家鄉有位女子,正在等他,但無奈人已深陷江湖,身不由己,況且當時年少得志,也著實捨不得到手的權勢,於是便應下了婚事。成婚起初幾個月,兩人還算相敬如賓,但漸漸各自都露出了本性。在他眼中,姚俐為人蠻橫無理、心胸狹窄、不解風情、庸俗難耐,說話尖酸刻薄、盛氣凌人,仗著是大公子的人,對他頤指氣使、作威作福,兩人感情一落千丈,相看生厭,形同陌路,夫妻關係早已有名無實,全因大公子的關係,才勉強生活在同一個院子裡。
再加上,正如大公子當時所料,青雲宮發下來的許多命令,他都無法苟同,但青雲宮的命令一向沒有商量的餘地。他懊悔當年的種種抉擇,但卻為時已晚。這些年來,懾於青雲宮的淫威,他昧著良心,一一服從,但心中清楚,必須及早謀劃一條退路了。
而對姚俐而言,她也一樣忍無可忍。她心中其實恨不得有朝一日,抓住丈夫對青雲宮不忠的把柄,好叫大公子出手斃了,她也好早日從苦海中解脫出來。所以當日發現那鹽包藏銀案有些蹊蹺,便緊抓不放,一邊試探丈夫口風,一邊更派手下心腹四處調查。白行舟雖自信已抹乾淨了痕跡,但長此以往,終究不是辦法。除了鹽包藏銀案,要是讓她翻出舊帳,再查出其他事情來,可就不好辦了。
書說回頭,卻說雲菲語沒聽說過什麼「鏢局的案子」,一臉不解,白行舟說道:「不重要。菲語,你只需要知道,我已下了決心,很快便會動手。那潑婦,得意不了幾天了!」
雲菲語奇道:「動手?你……你想幹什麼?」
白行舟再喝一碗,烈酒下肚,人膽也壯,他語氣冰冷而堅定,說道:「我要殺了那潑婦,擺脫大公子的掌控!」
雲菲語大驚,「殺、殺了夫人?可、可是,舟郎說過,大公子的勢力,無處不在!」
白行舟神色冷峻,說道:「菲語,你不必憂心。我跟隨大公子多年,對他的勢力瞭如指掌,我知道該怎麼做,才能躲過他的追蹤!我已籌謀多年,暗中積攢下了足夠的財富,安排好了退路,做好了萬全的準備!」
「退、退路?」
「沒錯!」白行舟緊握雲菲語雙手,說道:「菲語,我曾說過,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,我不會食言。我殺了潑婦,便帶你離開汀鎮,遠走高飛!」
「離開汀鎮?」雲菲語驚詫再問:「那舟郎的五渡堂呢?」
白行舟哼了一聲,「這有名無實的總舵主,不當也罷!」他一頓,臉色變緩,問道:「菲語,離開以後,我便不再是那江南武林第一人了,你可會嫌棄我?」
雲菲語急道:「舟郎什麼話?菲語一向但求過些平凡日子,從不在乎那些!」
白行舟點頭苦笑,「平凡的日子,才是最難得的。我經歷了多少,才明白這番道理?這一層,我不如菲語呀!」
雲菲語思緒一片混亂,思忖了片刻,才又問道:「那,舟郎,我們要去哪?」
白行舟語氣神秘,卻自信滿滿,說道:「你不必多問,我已安排好一切。菲語,你雖不在乎名分,但我卻要你堂堂正正,當我的夫人!到了落腳之處,我再給你買一家繡坊,你可以重開新的翠雲閣,我則買一家書院,興許,當個教書先生。你我從此歸於淡泊,長相廝守!菲語,你可信我?可願意跟我走?」
雲菲語毫不猶豫,「菲語相信舟郎!菲語是舟郎的人,無論舟郎去哪,菲語自當相隨!」
「好!」白行舟大喜,烈酒滿上再乾,臉色突然變得嚴肅,說道:「菲語,你記住我的話,接下來,我會離開汀鎮,這兩天裡,你做好準備,兩日之後,晚上此時,帶上簡單行囊,你我在鎮外月老廟相見!」
雲菲語怔怔點了點頭,重複道:「兩日之後,晚上此時,鎮外月老廟,菲語記下了!」
世上又有哪個女子,當真不要名分?倘若從此果然能與情郎光明正大、雙宿雙棲,雲菲語又怎能不歡喜?她凝視著情郎,眼中滿是興奮與憧憬,白行舟輕撫著她臉龐,按捺不住,湊前吻下。雲菲語輕輕「嚶」了一聲,手臂不由自主纏上了情郎脖子。
院牆之外突然傳來一聲異響,雖然輕微,卻逃不過白行舟的耳朵。他心中一凜,放下了雲菲語,倏地翻牆衝了過去,四下一望,卻看不見半個人影。
「莫非,是我喝多了?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