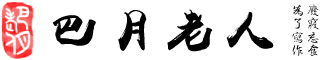弦斷笛續
夕陽西斜,昏鴉歸巢。
這是秦藏鋒與秦弦月在新墳旁度過的第一天。
秦藏鋒領著秦弦月,在竹林中慢步走著。秦藏鋒問道:「玦兒精通音律,她沒有教過你嗎?」
秦弦月憶起往事,眼眶又紅,答道:「小時候,娘教了,我當時叛逆,不願意學。後來想過要學,卻一直拖延,總以為,來日方長。」
秦藏鋒沒有多言,挑中了一株苦竹,拔劍一削,砍下了一段。桐琴被毀後,長風劍便只懸在腰上。他撿起竹子,掂量端詳,竹子筆直,厚薄適中,其色淡綠,比拇指略粗,比兩尺稍短,一端有節,一端開口。他滿意點了點頭,又舉起長風劍,在竹身上鑽開了七個小孔。三尺長劍,在他手上宛如精雕刻刀,落刀精準,分毫不差。最後收劍,拇指凝聚內力,把孔口、切口等處一一磨滑,連秦弦月也看出來了,這是一把橫笛。
他把橫笛湊到嘴邊,輕輕吹起。笛聲清亮悠遠,如山間晨風掠過松梢,又似高空孤鶴振翅長鳴。
秦弦月雖自稱不懂音律,但在戲班裡見多了,也有些見識。她說道:「若能再加上笛膜,音色便更明亮清脆了。只可惜眼下,取材不易。」
秦藏鋒道:「錦上添花,可有可無。音律之道,追求隨性自然,天人合一,若凡事苛求極致,便成執念了。」
他琴藝通神,但隨身攜帶的,卻也只是一把尋常桐琴,其理便在此。說起執念,兩人又想起了寒如玦,不禁又一陣黯然。秦藏鋒情至意起,緩緩轉身,吹奏出一曲《空山夢語》,曲調淒清,回旋徘徊,似夢似幻,情意綿長,追憶故人,淚已落,情難斷。
此曲催人落淚,曲終,秦弦月才驚覺已淚流滿面。她輕輕擦拭,擠出笑容道:「知先生擅琴,原來笛亦精通。先生桐琴已毀,此笛正好替代。」
秦藏鋒道:「彈琴吹笛,不過是『技』;樂理音律,方為『藝』。藝若通,技,不過是生熟之別而已。」
秦弦月若有所悟,暗暗沉思。秦藏鋒又道:「不過,這把橫笛,並非為我而製,而是給你的。」
說著,他輕輕一拋,交了給秦弦月。秦弦月接下,奇道:「給我?」
秦藏鋒輕輕一笑,神采變得飛揚,說道:「學技容易,學藝也不難。技藝純熟後,便能學『道』。道若通,笛與劍,便能合一。曲調便是劍勢,曲意便是劍意!」
秦弦月怔了片刻,才問道:「先生這是,要傳我武功?」
秦藏鋒道:「先教音律,再傳劍法。你可願意學?」
秦弦月反問:「先生不怕?」
「怕?」
「怕我用先生的劍法,去殺世上負心之人。」
秦藏鋒莞爾一笑,說道:「數日相處,幾番爭辯,你的確像是個草菅人命的女魔頭。不過昨晚之後,我便明白了。你說過的話,只是台詞,你弄紅塵殺過的人,出手的都是玦兒。你,沒殺過人。」
「你怎麼看得出來?」
「因為我殺過人,殺過不少人。」
秦弦月沉默了。自懂事以來,她做的是娘親吩咐的事,說的是娘親教導的道理,看著娘親拔劍殺人,她從來不曾想過對錯。直到遇上了秦藏鋒,她才驀然發現,原來還有另一條路可走。如今娘親不在了,她雖不知道今後該往何處去,但卻至少可以肯定,今後所做的事、所說的話,都會是她自己的心意、自己的道理。
眼下便是第一個屬於她自己的抉擇。
能得七弦劍仙傳授一招半式,終身受用不盡,這種機緣,江湖上多少人求之不得?但秦弦月卻垂下了頭,沉吟不決。先說音律,除了寒如玦,戲班之中,便有四位樂師,她若想學,何須等到今日?再說劍法,寒如玦的武功,不在白行舟之流之下,這些年來,為了方便弄紅塵行動,雖逼著她練了不少,但她也始終覺得索然無味。此時眼前的若是別人,她想必已一口回絕,但秦藏鋒卻不是別人。兩人雖都沒有說破,但彼此心知肚明,血濃於水。樹欲靜而風不止,她不想重蹈覆轍。所以她點了點頭,「好,我願意學。」
——
兩人在小丘上的第二天,秦弦月立於崖邊,橫著笛子,吹奏了一曲。曲終,她回過頭來,望著秦藏鋒,眼中帶著怨氣。
秦藏鋒臉上似笑非笑,點點頭道:「不錯,難聽死了。」
秦弦月反唇譏道:「都說名師出高徒,果然不差!」
秦藏鋒笑道:「學了一日,能有這般成績,已屬難得。世上技藝,從無一蹴而就,唯一法門,四字真言:勤學苦練!」
秦弦月無奈長嘆。秦藏鋒又道:「昨日教了你五音之調,你雖未純熟,但只要謹記口訣,日後不難慢慢練習。今日,便教你五音之勢!」
「音也有勢?」
「當然有。」秦藏鋒拔劍出鞘,說道:「看清楚了!」
他口中一邊解釋,手上一邊出劍,以音意引劍勢,又以劍勢演音意。
「宮」為五音之首,居中統御,沉穩大氣。宮之劍勢,穩重如山,劍路正大,不偏不倚,似堂堂王者,光明正直,氣勢渾厚,無可躲避。
「商」音剛烈肅殺,音質銳利。商之劍勢,劍風如鐵,勢如雷霆,以鋒銳破敵,以速度致勝,遇敵即決,無留情餘地。
「角」音象萬物始生、春雷初動,其勢開張靈動,如萬象更新,變化莫測,不拘一格,虛實交錯,引敵破形。
「徵」音高亢激烈,情動呼號。其勢如歌如嘯,起伏驟變,殺機藏於狂態之中,以奇招制敵、借勢而為,疾如奔馬、忽轉如鳶。
「羽」音柔和清遠,幽情空靈。羽之劍勢,輕靈飄渺,動如煙雲,避實擊虛,劍隨影走,如夢如幻。
(作者注:角,在此音「覺」;徵,在此音「指」。)
秦藏鋒接著又即興演示了一套劍法,一邊解說道:「五音相混,便成曲,五勢相交,便成招,其理相通。無論是吹笛還是用劍,五音皆非孤立,講究的是調和之理,互轉互補、互化互變!看我劍法,以宮為主,運商破陣,借角開局,以徵激勢,終羽斷魂!」
最後一劍,揮出了一道劍氣,丈許外幾株竹子,斷裂倒下。他回劍入鞘,問道:「看懂了嗎?」
秦弦月閉目沉思,過了良久,抬頭問道:「我連音律都尚未學純熟,先生是否教得太急了?先生,是趕著離開嗎?」
語氣之中,隱隱藏著傷感。秦藏鋒沒有回答,只說道:「音律講究記好,音調講究練熟,音勢,講究領悟。能學多少,便看你悟性了。」
——
第三天,又是黃昏時分,殘陽如血。
在那座新墳旁,秦藏鋒與秦弦月過招練劍。秦弦月用的,是娘親留下的軟劍,使的也是一樣的劍法,雖不如寒如玦精純,卻也不失神髓。
兩人打了上百招,秦弦月已漸感氣喘,秦藏鋒卻仍氣定神閒。他微微一笑,還劍入鞘。秦弦月略感不服氣,哼道:「這就夠了?我還可以再打三百回合!」
秦藏鋒搖頭苦笑,就像一個父親對淘氣的女兒,束手無策。他問道:「玦兒的這套劍法,招式凌厲決絕,可有名字?」
秦弦月答道:「娘親說過,劍法名叫『絕情』。」
秦藏鋒心中一嘆,劍如其人,一個如此癡情的人,為何會如此絕情?
他甩了甩頭,又道:「你已能把五音劍勢,融入劍招之中,不錯,但領悟未夠深切。所以音律不能荒廢,你笛子吹得越好,劍法也會更高。當你笛子上的功夫,有你弄紅塵那位繞樑姑娘的修為時,在江湖上便很難遇見敵手了。」他一頓,又道:「但是,這還不是我真正的劍法。」
秦弦月想了想,說道:「你與白行舟交手那一晚,那一劍,才是你真正的劍法。」
秦藏鋒點頭道:「就如彈琴。五音彈得再準,調不成曲,也是雜音。當你能把劍勢調和成曲時,便能孕出劍意!劍意如曲意,能感染人心,所向披靡。我的劍法,名叫『琴心劍意』,劍招融於劍意,劍意發自琴心,一般人,學不來。但你,可以。」
「我?為何?」
秦藏鋒回憶道:「那一晚,你能感悟到我的劍意,更能憑心哼出與劍意相剋的曲子,這便說明,你有天賦。」
「那你何時教我?」
秦藏鋒搖頭笑道:「這種境界,只能意會。我能教你的,都教完了。」
秦弦月聞言,忽感一陣失落,說道:「正好,已是第三天。所以,你要走了?」
秦藏鋒仰天閉目,神色平靜如水,沉默良久,才緩緩說道:「天底下,有兩種人,一種是男人,一種是女人。男女之間,既是伴侶,也是敵人,在情場上,勾心鬥角,相愛相殺,卻又誰也離不開誰。」他長嘆了一聲,語氣變得悲涼落寞,說道:「弦月,我不走了。」
「不走?」不走本是好事,但秦弦月卻隱隱有不祥的預感。
秦藏鋒點點頭,說道:「我已決定,要去見玦兒了。」
秦弦月心頭一震,又氣又急,頓足道:「你何必如此!」
秦藏鋒卻很平靜,他緩緩說道:「弦月,我已深思熟慮,不是一時衝動。從二十多年前起,我活著,便是為了尋她。我尋她,是為了向她證明,我對她用情至深。她為了守護心中純潔無暇的感情,不惜一死,無論在外人看來,多麼偏激荒謬,我也始終愛她敬她。所以,我也願意成全她。黃泉相見時,我會對她說三件事。第一,我的心,已不會再變;第二,我也可以為她所守護的感情而死;第三,」他一頓,轉頭看著秦弦月,繼續道:「我要感謝她,為我生養了一個好女兒。」
秦弦月心情悲痛,卻萬般無奈,只好罵道:「瘋子,你們都是瘋子!」
秦藏鋒淡淡一笑,說道:「台上唱戲的,是瘋子,台下看戲的,是傻子,世人,其實都一樣。弦月,你不必為我傷感。三日之前,我從不知道你的存在,也不曾盡過半點為人父的責任,我不期望你對我,有父女之情,我只盼你莫要怨恨我,也莫要怨恨玦兒。你便當是,看了一場鬧劇,曲終之時,人總得散。」
秦弦月默默聽著,不知不覺,淚已落下。
秦藏鋒又道:「我最後還有三個不情之請,希望你可以幫我完成。」
夕陽西沉,餘暉斜照,天色漸冷,萬物將沉。風吹殘葉,瑟瑟作響,似無奈的嘆息。
「第一,這把長風劍,乃是一位故人托我保管,我答應以性命守護,但性命如若已不在,這承諾也就不作數了。你幫我把它,沉入汀河之中便是。切記,莫要被人看見。」
「第二,你已長大,該有自己的生活。我希望你,莫再糾結於玦兒的執念,莫再束縛於弄紅塵的使命,從此好好為自己而活。」
「第三,把我,葬到玦兒身旁吧。」
——
夜色如水,江上一條客船,搖搖擺擺,逆水而駛。
船上除了艄公,便只有一男一女,兩個客人。
艄公在船尾撐船,客人在船艙歇息。船艙內,點了燈火,男的,是白行舟,女的,是雲菲語。
雲菲語側臥地上,似已睡著,白行舟盤膝而坐,盯著雲菲語背影,眼神複雜。
青雲宮眼線眾多,他們要去的地方極為隱秘,他花了無數人力物力,才安排好了這一條退路,倘若走漏了風聲,下場不堪設想。
可是,雲菲語還信得過嗎?她能出賣他一次,難道不會有第二次?
白行舟不敢冒險。在性命與愛情之間,他作出了選擇。
他雙手藏於袖中,無聲無息,一指擊出。但在出手的那一瞬間,他卻看見雲菲語手腕上,綁了一條青絲帶。
兩人用作信號的那條青絲帶。
一條尋常不過的青絲帶,甚至還有點髒污,但雲菲語卻帶上了。
那一瞬間,他猶豫了。他的指勁偏了分毫,打在雲菲語身上,便偏了兩寸。
雲菲語一陣吃痛,驚醒過來,口吐鮮血,看著情郎,滿臉驚異,不敢置信。
白行舟悲痛懊惱,柔聲說道:「菲語,讓你受苦了,這一次,我不會再失手!」
他正想再補一指,船艙門口卻突然出現一條人影。
此人身材高大,身披斗篷,面目深埋在黑暗之中,看不清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,很是神秘。
他一言不發,踏前一步,半張面目暴露了在燈光之下。
白行舟認出來人,驚道:「是你!老……!」
一句話沒說完,人便死了,死在了斗篷人掌下。
雲菲語驚怒攻心,傷勢加重,昏厥過去。斗篷人沒有再理會白行舟,轉身蹲下,探聽雲菲語脈搏,彷彿輕嘆了一聲,然後把雲菲語扛了起來,腳一蹬,飛出了船艙,踏江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