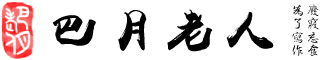真假慈悲

劍光一閃,繩索應聲而斷,慈悲但覺身子一輕,大叫一聲,掉落地上,摔了個四腳朝天。雪球撲上前,又吠又舔,彷彿在心疼主人。秦弦月不想再逗留,回身正想繼續上路,慈悲爬起身叫住道:「女俠且慢走!請教女俠尊姓大名?」
秦弦月腳下不停,頭也不回,學著秦藏鋒的口氣,冷冷道:「我姓秦!」
慈悲快步跟上,聞言心頭突然一震,雙眼不由自主,再次盯上了秦弦月背上那麻布緊裹的長劍。他極力克制心中激動,說道:「原來是秦女俠。阿彌陀佛,女俠救了貧僧,貧僧無以為報,只好在佛祖像前燒香,禀報施主功德。」
秦弦月邊走邊哼道:「免了,我出手,全是看在你那忠犬的份上。」
雪球似懂人言,奔上前繞著秦弦月轉了幾圈,停在她腳下,又嗅又舔,搖尾輕吠。秦弦月忍不住停下腳步,蹲下輕撫。她看不清慈悲的真假,卻自問還看得清雪球的赤誠。白犬似有靈性,能叫牠忠心不二,說不定這和尚也不是壞人?說不定她看錯了?
慈悲心中一動,趁機說道:「善哉、善哉,經中有云,眾生皆有佛性。雖是畜牲,卻也懂得感恩。這條白犬,名叫雪球。自出娘胎,便父母雙亡,貧僧不忍,遂撿來撫養。如今兩歲有餘,與貧僧情同父子。」
秦弦月失笑道:「出家人,談什麼父子?」
慈悲臉有慚色,嘆道:「秦女俠責備得是,貧僧六根未斷,難以成佛,所以還得修行。」又問:「秦女俠這是要上龍山?是禮佛還神,還是遊山玩水?」
秦弦月臉色一沉,轉頭瞟著慈悲,冷聲問道:「你打聽我的行蹤,有何意圖?」
慈悲苦笑嘆道:「秦女俠的疑心病又犯了。阿彌陀佛,經中有云,知恩報恩,福德無量。貧僧沒有惡意,只是不敢落於狗後,想報答女俠出手相救的恩德罷了。山上廟宇道觀眾多,女俠若不識路,容易迷失。女俠想去哪家廟宇?廣覺廟、寶蘭寺、慈智宮?還是道觀?三聖觀、七星洞、八仙宮?又或是想走訪六月雪塢,尋人探親?貧僧都可指路。」
他長篇大論,秦弦月早聽得不耐煩,正想打斷,突然卻心中一動,問道:「六月雪塢?那是什麼地方?」
慈悲心中一喜,臉上卻不動聲色,答道:「那是山裡一條小村莊,地處偏僻,不易尋找。貧僧正想要進塢辦點事,女俠若想去,正好可與貧僧同行。」
秦弦月想起艄公的話,「夏飛霜」不正是「六月雪」嗎?心中又驚又喜,起身道:「好,那你帶路。」
慈悲道:「善哉、善哉,貧僧能幫得上忙,自是樂意。但此去六月雪塢,還得有小半天路程。如今天色已晚,入夜後,山路可不好走,更何況雪還未停。女俠何不到敝廟歇息一晚,等天明再一起上路?」
「到你的廟去?」
「是的。敝廟不遠,只在半里之外。」
——
慈悲的「廟」,原來只不過是幾間簡陋的茅屋。唯一像「廟」之處,便只有正中那「佛堂」之中,果然供著一尊泥菩薩。
秦弦月跟著慈悲,來到這廟前時,天已暗了下來,雪勢卻漸漸變大。秦弦月皺眉問道:「這幾間茅屋,倒比得上戲臺上的布景草棚、紙糊門窗。這便是你的廟?廟裡只有你一個和尚?」
「是的。」慈悲答道:「貧僧修的是孤禪,向來獨處,只有雪球相伴。」
孤禪講究清苦,茅屋陳設果然簡樸,但院子裡卻有一盆九里香,花正盛開,清香撲鼻,花瓣雪白,像地上積雪,又像雪球毛色,花蕊一點黃,艷而不俗,為院子增色不少。
慈悲道:「秦女俠可在貧僧的禪房歇息,貧僧在佛堂打坐即可。」
秦弦月眼珠一轉,卻道:「不必,我睡佛堂。」
慈悲也不爭,便把秦弦月領進了佛堂,回頭又搬進來一隻火盆以供取暖,然後在佛像前雙手合十,默默念了幾句,又上了一炷香,然後說道:「貧僧方才向佛祖說了,秦女俠拔劍救人,功德無量,求佛祖保佑女俠,一夜安枕。貧僧這便退下,女俠請自便。」說完,便退了出去。
秦弦月關上了大門,心中總算踏實了些。看這和尚,透著怪異,但又看不出有害人之心。走了一天,也覺疲累,在火盆旁靠牆坐下,正想吃點乾糧,忽覺睡意來襲,本只想合眼片刻,卻不知不覺,便已沉睡了過去。
——
遠處傳來雞鳴鳥歌,秦弦月猛然驚醒。
四下一看,自己還在佛堂之中,大門依舊緊閉,一切彷彿都沒有改變。她試一運氣,體內真氣通暢無阻,頭不疼,喉不燥,絲毫沒有中了迷藥的跡象,但昨晚怎會突然入睡?感覺還睡得極好,精神飽滿,難道當真是身體太累了?還是佛祖果然顯靈保佑了?
她心中一動,伸手一摸,長風劍還在。她放心不下,又扯開了麻布一角,偷偷一看,那劍首晶石依舊晶瑩剔透,輝如青天,的確還是長風劍,如假包換。
突然門口傳來一聲低吟:「阿彌陀佛。」
她暗暗一驚,忙把麻布重新包好,再三檢查,沒有破綻,這才整了整衣衫,推門出來。只見天已大亮,雪也停了,慈悲佇立院子正中,雙手合十,揹著個簡單的行囊,也不知已等了多久,此時見到秦弦月,便說道:「秦女俠早。天色已亮,女俠倘若還要去那六月雪塢,這便可以動身了。」
秦弦月點了點頭,正想說話,突然一皺眉,指著院裡那盆九里香問道:「花怎沒了?」
只見本來盛開的白花,果然全消失了。慈悲神色自若,說道:「阿彌陀佛,花開一瞬,花謝一瞬,花亦如人,榮枯如夢。經中有云,若見無常,心不動搖。」
秦弦月被他念得心煩,只好揮了揮手,說道:「算了、算了,出發吧!」
——
下了小半夜的雪,一走出茅屋小廟,只見雪壓枝頭,天地如洗,目光所及,地上都鋪滿了一層柔滑白雪,陽光透進林隙,林子一片靜謐。
所幸雪不厚,走起來並不難。慈悲在前頭帶路,雪球緊跟在旁,精力旺盛,前後奔跑,遠看便像雪球一樣,來回滾動。秦弦月則不近不遠,跟在後頭,心中猜測著艄公指點她去六月雪塢的用意。
走不多時,漸漸上山。山路本就崎嶇,被白雪一蓋,更是難走。好在慈悲與雪球果然都對此地很是熟悉,總能在一片白茫茫中找到山路。
上山不久,慈悲突然停下,轉身望著林子深處,口中念念有詞。秦弦月走近,順著他目光看去,只見一條山貓匍匐在地,突然四肢猛蹬,撲向前方一隻白兔。白兔倉皇躍起,未及三尺,便被山貓利爪攫住後腿,重重摔落地上。山貓張口咬住兔頸,利牙深陷,白兔掙扎不過數息,便氣絕身亡。山貓叼著白兔,拔腿一奔,瞬間消失在灌木叢間。
秦弦月嘴角一笑,調侃道:「和尚不是自詡慈悲嗎?怎見死不救?」
慈悲道:「秦女俠可還記得那株九里香?花開是道,花謝也是道。白兔吃草是道,山貓捕兔也是道。經中有云,眾生自有天性,順道方為慈悲。山貓捕食,只為果腹,救了白兔,豈非便害了山貓?」
秦弦月若有所悟,一言不發。慈悲雙手合十,突然念了起來:「南無阿彌多婆夜,哆他伽多夜,哆地夜他,阿彌利都婆毗,阿彌利哆悉耶那婆毗……」
一番嘰里咕嚕,念了許久,秦弦月忍不住打斷問道:「你這念的是什麼?」
慈悲恍若未聞,直到念完,才抬頭答道:「貧僧念的是《往生咒》,超渡白兔亡靈,祈願阿彌陀佛慈悲接引,令一切眾生,速生極樂國土。」
秦弦月輕嘆,幽幽道:「死都死了,超渡有用嗎?」
慈悲道:「真正要渡的,不是死者,而是活人。」他一頓,又道:「實不相瞞,貧僧幾天前作了個夢,夢見那六月雪塢,有亡靈哭泣,自那天起,便寢食難安。今日立冬,萬物收藏,想那亡靈卻仍飄泊於野,著實不忍。這一趟進塢,既是為了超渡那死者亡靈,也是為了讓貧僧自己心安。」
秦弦月皺眉道:「不過一場夢,也作得了數?」
慈悲道:「進了塢,一看便知。即便沒有,便只當為秦女俠領路,走一趟,也不虧,善哉、善哉。」
——
又走不久,已到了山腰,來到山坳處,正好可以躲避冷冽山風,兩人坐下歇息片刻。
秦弦月拿出幾塊肉乾吃下充飢,慈悲也從行囊中拿出一個饅頭,一邊吃著,一邊又打開一個油紙包裹,裡面原來竟是一塊生肉。
秦弦月見狀,忍不住又調侃道:「一個和尚,行囊中竟帶著生肉,也不怕犯戒?」
慈悲輕笑道:「秦女俠與貧僧都要進食,雪球不過凡狗,自然也一樣。」
說著把生肉一拋,雪球一口叼住,便大快朵頤,吃了起來。
秦弦月哼道:「那這生肉從何而來?你豈非犯了殺生之戒?」
慈悲道:「這是雪球自己捕獵得來的野雞,貧僧只負責切肉。」
「切肉之前,也念《往生咒》?」
「那是自然。這與山貓捕兔,是一般道理。」
這道理不難,但秦弦月心中不服,眼珠閃過一絲淘氣之色,故意為難,說道:「我記得聽過一個故事,一頭猛鷹正捕獵一隻白鴿,白鴿飛到一位國王腳下求救。國王為了救下白鴿,便割下自己身上的肉,餵食猛鷹。看來你的慈悲之心,比不上那國王。」
慈悲微微一笑,不慌不忙,說道:「秦女俠的故事,只說了一半。那位國王,王號叫薩波達,猛鷹及白鴿,其實是天帝釋及邊王所化,旨在試探薩波達王的心志。他們使用法術,令薩波達王割盡身上所有血肉,卻始終湊不足白鴿的重量。直到薩波達王將死,他們才被國王的無上志願所感動,現出原形,並再用法術使國王重新長出血肉,精氣神反更勝從前。」他一頓,才淡淡一笑,接著道:「所以這個故事,只不過是一則寓言神話,不存在於人世,當不得真。」
秦弦月一怔,想不到反駁的話,只好又問道:「那真實人世又如何?」
慈悲想了想,答道:「天底下,有兩種人,一種真慈悲,一種假慈悲。」
秦弦月心中一凜,訝異問道:「這句話,你從何處聽來?」
「哦?」慈悲反問道:「難道除了貧僧,還有人說過這句話?」
「當然有。」秦弦月揚眉道:「他是一位前輩高人,他的本事,你做夢都想像不到。」
慈悲心中發笑,淡淡道:「貧僧也認識一位聰明絕頂的高人,雖然沒什麼本事,但這句話,卻是他的口頭禪。女俠說的那位前輩高人,說不定也是從別處聽來的。」
秦弦月悶哼了一聲,不想再追究,接著問道:「算了,那你說,何為真慈悲,何為假慈悲?」
慈悲微笑道:「那貧僧也給秦女俠說個故事。卻說某山腳下有條村莊,山上有條白額猛虎,常闖進村里吃人作惡。村民集結人馬,上山獵虎,幾經艱難,終於把猛虎殺死,但卻在虎穴之中,發現一條虎崽子。本想斬草除根,此時村子一個和尚卻突然趕到,說虎崽子尚幼,不曾害過人,不可濫殺。村民見虎崽子幼小可憐,體型還比不過山貓,也於心不忍,但倘若不殺,又恐有後患。和尚於是自告奮勇,抱起虎崽子,遠走千里,去到一處深山野林,才把虎崽子放生。他回到村子後,村民都讚他菩薩心腸,慈悲為懷。他們卻不知,五年之後,那虎崽子長大了,還是一樣兇猛嗜殺,闖進當地的村莊中,又殺害了更多人命。」
他說完一頓,又繼續解釋道:「人世間,凡是慈悲,都有代價,只看代價大小,以及由何人償付罷了。經中有云,惻隱之心,人皆有之。但世人卻往往只會憐憫眼前看得見的苦難,而對千里之外、百年之後的苦難置若罔聞。救兔殺貓、縱虎歸山,凡此種種,都是不曾顧及代價的假慈悲,所求不過自己一人心安理得。只有權衡過全局,忍痛作出取捨的,才是真慈悲。」
秦弦月側頭想了想,說道:「你的意思,要行真慈悲,就得犧牲白兔及虎崽子?你這番話,不像佛陀的道理,倒像君王的權術!」
慈悲一笑,說道:「經中有云,一切眾生,悉有佛性。眾生平等,君王亦可成佛。權術可使天下歸己,亦可使天下離苦,是佛是魔,全在一念之間。若能渡眾生,又管它是佛法還是權術?」
這番似是而非的道理,不禁叫秦弦月心中嘀咕。眼前這人到底是個離經叛道的真和尚,還是個披著僧袍的假和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