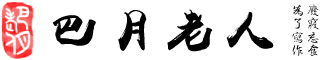諸相非相
秦弦月口吐鮮血,臉色慘白,撐著劍搖搖晃晃爬了起身。
她手中撐著的,正是從司徒不平身上奪回來的長風劍!
她冒險一搏,雖然不盡如意,受了對方一掌,但最終卻還是成功奪回寶劍。她擦乾了嘴角鮮血,雖仍覺五內翻騰,四肢無力,自知內傷不淺,卻還是忍不住得意地笑了出來。
「你姓秦?」司徒不平臉色凝重,沉聲問道:「七弦劍仙秦藏鋒的後人?」
秦弦月喘著氣笑道:「你能認出我的劍法,更被我逼得使出真功夫,說明本姑娘沒有白練,也沒有丟他老人家的臉!」
司徒不平瞳孔一收,語帶怒意,繼續質問道:「原來是劍仙偷了我青雲宮的長風劍?他為何要這麼做?」
秦弦月笑著反問:「大公子好本事,何不自己去問他?」
秦藏鋒已不在人世,此話是繞著彎子罵人,但司徒不平卻不知內情。他冷哼一聲,說道:「看在劍仙前輩的面子上,把劍留下,本公子讓你走!你回去給他傳話,竊取本門聖物,青雲宮絕不輕饒,終於一天,本公子必親自登門問罪!」
秦弦月氣道:「本姑娘才不會為你傳話!」她厭惡司徒不平盛氣凌人,言辭中對秦藏鋒更語帶不敬,此時雖身陷險境,心中卻還是忍不住淘氣心起,高舉寶劍,故意刁難道:「這把劍既然是青雲宮聖物,那大公子見我持劍而來,為何不跪?倘若任你肆意搶奪,那這把劍又何聖之有?」
「大膽!」司徒不平勃然大怒,冷聲說道:「既然你冥頑不靈,那本公子就不客氣了!」
天底下沒有幾個人敢不把青雲宮放在眼裡,但七弦劍仙卻恰巧是其中一個,所倚仗的,自然是他堪以匹敵青雲宮武學的劍法。司徒不平見秦弦月已得他真傳,雖未成氣候,但假以時日,難說不又成隱患。此時秦弦月倘若能乖乖交出寶劍,尚可暫且留她一命,甚至收為己用,但既然執意與青雲宮作對,那便留不得了。當下動了殺機,話音方落,腳下一蹬,人便衝了上前,一掌拍出,誓要斬草除根,永絕後患!
秦弦月傷勢不輕,此時四肢乏力,根本已無法招架。正暗暗叫苦,突然一人一衝上前,把她扛了起來,逃出丈許之外,大叫道:「大公子息怒,掌下留人!」
秦弦月與司徒不平皆大感詫異,出乎意料,救人的卻竟然是郭大膛。司徒不平大怒斥道:「大膽!郭大膛,你也反我?」
郭大膛急道:「野丫頭不識抬舉,但心腸不壞,罪不至死啊!」又對秦弦月道:「丫頭!你聽聽勸,把劍留下!不值當把自己送上砧板,當待宰的肉!」
說著更伸手去搶劍,秦弦月偏偏性子隨父母,一身傲氣,吃軟不吃硬,拼命抱緊了長風劍,罵道:「痴心妄想!」
司徒不平喝道:「郭大膛!你聽見了吧,此人竊取我門聖物,罪不可赦!」
郭大膛一頓足,一咬牙豁了出去,突然掉頭便跑,扛著秦弦月拔足狂奔,喊道:「大膛先救人,回頭必把劍取回,再向大公子請罪!」
司徒不平氣極而嘆,嘆郭大膛不自量力,正要追上,突然身後傳來一陣破空之聲,忙回身伸手一抄,兩指穩穩夾住一枚暗器,仔細一看,原來竟是一枚琴軫!
他心中一凜,抬頭四下一看,卻不見有人。天底下有什麼人會用琴軫作暗器?若是平時,他多半想不起來,但此時此刻,卻不言而喻。他驚疑不定,忽覺背脊發涼,不敢輕舉妄動,緩緩抬手抱拳,朗聲說道:「敢問可是劍仙前輩到訪?何不現身一敘?」
他記得很多年前,曾經與秦藏鋒有過一面之緣,但對於此人的武功之深淺,卻只聽宮父轉述過。宮父曾說,此人的琴心劍意,即便是混沌無極功練到了第七重,也多半只能接下二十劍,天底下除了宮父的第八重神功,無人能敵!他今日見識過秦弦月的劍法,對此更不存疑。
強敵環伺在側,自己身受重傷,他不敢不謹慎。但等了片刻,四下靜悄悄地,卻根本無人應聲。他心下暗忖,難道劍仙的意思,只是要阻止他追殺那位姑娘?他再回頭一望,郭大膛扛著秦弦月,早已逃得無影無蹤,心下不由得懊惱不已,忿忿不平,明明已到手的長風劍,卻竟然得而復失!不但如此,環顧四周,美酒、肉湯倒灑一地,地上躺著四具屍首,黎空谷更是生死未卜,若非他僥倖破關,今晚難免在陰溝裡翻船,死於非命!好好一場立冬肉宴,竟樂極生悲,鬧得一片狼藉,叫他心裡恨得咬牙切齒!
他遭人下毒謀害,殺手埋伏刺殺,事出離奇,奇毒雖是藍無風所煉,但他卻隱隱覺得,幕後還有一隻黑手。難道果然是「他」?
——
郭大膛扛著秦弦月,拔足急奔。他的輕功算不上上乘,但勝在孔武有力,即便扛著一人,腳步也不慢。
秦弦月不斷掙扎,郭大膛忍不住邊跑邊罵道:「野丫頭,別再不知好歹,老子這是在救你性命!」
秦弦月哼道:「我去肉館,本是要找你算帳,你反要救我,演的又是哪一齣?」
郭大膛道:「老子坦蕩蕩,從來不演。救你只因你是個好人!」
秦弦月冷笑道:「我是好人?我一旦恢復了力氣,便要殺了你這無恥屠夫,為雪球償命!」
郭大膛失笑道:「你為了一條狗,便大發雷霆,自然是好人。你要殺老子,老子管不著,等你傷好了,你我再打一場便是!但老子那鋪子裡,豬狗牛羊死了無數,從沒死過人,今晚卻一口氣死了四個!那三個殺手罪有應得,死有餘辜,但姚總管卻死得冤。冤死一個已然太多,老子能救一個是一個!」
秦弦月聽他語氣誠懇,心中不禁動搖,問道:「既然自詡坦蕩,卻為何去強擄和尚的狗?你為了討大公子歡心,便可以不擇手段嗎?」
郭大膛怒道:「胡說八道!老子何曾去搶他的狗了?白天你離開後不久,是那和尚自行把狗帶來賣給老子的!老子真金白銀付了他五十兩銀子!」
秦弦月聞言,腦中猛然又「轟!」地一聲,彷彿又想明白了許多事情。
兩人邊說邊跑,此時已跑到了村口。夜深人靜,街上已不見行人,但前方卻突然有人現身,提著一盞燈籠,招手道:「這裡,快!」
兩人走近,凝神一看,此人僧袍髡髮,正又是慈悲和尚。他語氣著急,低聲叫道:「大公子馬上追來,快跟貧僧走!」
他神色緊張,彷彿情勢很是危急,說完拉起郭大膛,掉頭便走。郭大膛六神無主,也不多問,緊緊跟上。秦弦月本想喝阻,但轉念一想,又冷冷一笑,心中思忖,便儘管看看,你這自詡慈悲的假和尚,又還有什麼陰謀詭計。
慈悲在前面帶路,三人出了六月雪塢,卻不下山,反而沿著山路,越爬越高。昨夜的積雪已融化不少,但山路卻也一樣不好走。郭大膛腳步矯健,又早已習慣山里生活,走起來並不覺難,但慈悲此時卻也一樣健步如飛,完全不是一個文弱和尚該有的樣子。秦弦月看在眼裡,不動聲色,心裡卻暗暗冷笑。
不多時,山路走到盡頭,竟到了一處斷崖邊上,慈悲這才停下,說道:「善哉、善哉,此處離村塢已遠,應該安全了。」
此處四下環境荒涼,不見人煙,郭大膛放下了秦弦月,心慌慌地回頭張望,生怕大公子追上來。秦弦月見狀忍不住搖頭嘆道:「不必看了,根本沒有人追上來。」
司徒不平當然沒有追上來,他被一枚琴軫拖住,想追時卻已是太遲。那枚琴軫,自然是慈悲的疑兵之計。秦弦月雖然不曾對他袒露身份,但他卻早已猜到。長風劍本該在秦藏鋒手中,卻傳到了這位秦姓姑娘手上,兩人的關係,不言而喻。他一早準備好這枚琴軫,沒想到關鍵時刻,竟果然派上了用場。
但郭大膛卻聽不明白她弦外之音,也不想深究,他拍了拍胸脯,說道:「好了,姓秦的丫頭,老子說到做到,已把你救出險境。你把劍交出來吧,老子帶回去還給大公子,保證不會洩露你的行蹤!如此這鍋湯鹹淡正好、火候也到,兩全其美,你可別再不知好歹,挑嘴得過了頭!」
秦弦月傷勢不見好轉,在郭大膛肩上一陣勞頓,反而更覺內息渾濁,四肢乏力。她撐著坐直了身子,嘆道:「郭大膛呀郭大膛,本姑娘算是看出來了,你是個老實人,也是個好人,但卻不是個聰明人!」
郭大膛瞪圓了眼,怒道:「事到如今,你還想逞強?老子倘若硬搶,料你如今也攔不住!」
秦弦月不再理會他,轉頭瞪著慈悲,冷冷問道:「你到底是什麼人?」
慈悲雙手合十,說道:「阿彌陀佛,貧僧慈悲,秦女俠難道是傷勢太重,神智迷糊了?」
秦弦月冷笑道:「不迷糊,本姑娘如今才剛清醒過來。慈悲和尚,不過是你台上一個角色,你台下本相,半點也不慈悲,更多半不是個真和尚!」
慈悲神秘地微微一笑,說道:「經中有云,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,若見諸相非相,即見如來。那秦女俠認為,貧僧本相,是什麼人呢?」
秦弦月瞳孔一收,沉聲說道:「事已至此,你又何必再裝?我若沒猜錯,你就是,」她一頓,一字字道:「小公子!」
「小公子?」郭大膛吃了一驚,問道:「大公子的兄弟?小公子?」
「秦女俠好眼力。」慈悲和尚,或者說,司徒不凡,仰天哈哈一笑,坦然承認,反問道:「敢問秦女俠,是如何推斷出本公子的身份?」
秦弦月道:「你處心積慮,要謀害大公子,天底下除了小公子,何人有此膽量?」
司徒不凡搖頭笑道:「江湖上想取司徒不平性命之人,豈在少數?你方才親眼所見,毒夜叉藍無風便是其中之一。」
秦弦月道:「小公子何必過謙?她也只是受你指使。她煉毒,你下毒!」
司徒不凡聞言,不禁搖頭苦笑道:「本公子與藍無風,到底是誰受誰指使,還真說不清。不過也沒錯,我按她的藥方,為今晚這一場肉宴,可籌備了將近四年的時間!」
郭大膛聞言,勃然大怒,驚道:「是、是你下毒害大公子?你、你們不是兄弟嗎?你為何要這麼做?」
兩人都沒有理會他,秦弦月繼續說道:「我還聽說過,小公子心計深沉,陰險狡詐。你臥薪嘗膽,忍辱負重,四年下一毒,甚至不惜削髮假扮和尚,所作所為,正符合這番描述!」
司徒不凡摸了摸光禿禿的頭頂,苦笑嘆道:「慚愧、慚愧。本公子若不喬裝一番,只怕難逃司徒不平的耳目呀。」
秦弦月也嘆道:「有人也提醒過我,要對你多加提防,只可惜我還是大意了。沒曾想,本姑娘在弄紅塵戲弄過無數人,今日終於還是著了你的道,入了你的戲,這可真是現世報呀!」
「哦?」司徒不凡揚眉問道:「如此說來,秦姑娘是如何掉進本公子的圈套裡,如今都想明白了?」
秦弦月點點頭,說道:「你我在山腳樹林相遇,你被吊在樹上,但其實,我才是那一腳踏進陷阱之人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