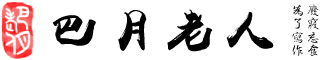玉瓦俱碎
「當時,你演了一齣《紅孩兒》裡的吊樹引唐僧,」秦弦月輕輕一笑,說道:「不過這等把戲,卻瞞不過本姑娘一雙火眼金睛。」
「沒錯,」司徒不凡坦言道:「你起初不上當,我真有些急了,但你卻偏偏因雪球而心軟,讓我得逞了。」
「但我卻想不明白,為何是我?」
司徒不凡大笑答道:「你用麻布纏裹長風劍,瞞得過別人,卻瞞不過親眼見過長風劍之人。司徒不平一眼看透,本公子亦如此。我為司徒不平準備的毒藥,萬事俱備,只欠東風。時間緊迫,我正心急如焚,你便正好及時出現。你背上的長風劍,便是本公子的東風!」
一切都如周天算所預言,他的貴人,自南而來,他一眼便能認出來。秦弦月輕撫著手上的長風劍,心中卻在想,當天那名神秘艄公,似乎對長風劍所知頗深,卻為何不提醒她?難道就是有意要讓小公子認出劍來?她又繼續說道:「你留我在廟裡過夜,就是為了要在長風劍裡做手腳。」
「沒錯。」司徒不凡神色有些得意,笑道:「我把那盆九里香花瓣,塞進了劍鞘之中。我猜,你一定想不明白,你當晚為何毫無察覺?」
秦弦月皺眉道:「我當晚睡得極沉,醒來卻神清氣爽,我從沒聽過有如此一種迷藥!」
司徒不凡自豪道:「你當然沒聽過。這種迷藥,叫作『江湖一夢』,乃是我青雲宮獨門煉製,珍稀之極!」當年對付壺山獵戶楊百步,用的也是這種迷藥。他一頓,又笑道:「不過你放心,此藥對人體無害,更有助眠之效!」
秦弦月恍然,眼神又突然變得銳利如劍,直瞪司徒不凡,冷聲道:「但九里香卻只是你毒藥的其中一份。還有一份,是雪球!」
說起雪球,司徒不凡神色彷彿也變得黯然,緩緩點頭道:「沒錯,雪球犧牲了。狗為主人死,莫問值不值。養兵千日,用在一時,本公子從養牠那一天起,牠的命運,早已注定。」
人非草木,孰能無情,他彷彿也在極力說服自己,雪球之死,無可避免。但秦弦月卻不肯放過他,她破口怒罵道:「忠犬不二主,義士不二心。雪球對你忠心一片,但你為了下毒,竟不惜在牠身上動手腳,更親手把牠賣了給郭大膛,眼睜睜看牠被宰殺、熬成肉湯!你狼心狗肺,禽獸不如!」
司徒不凡深呼吸了幾口氣,極力平復了心情,才說道:「秦女俠,你可還記得,救兔殺貓、縱虎歸山的故事?雪球在你眼前犧牲,你心生憐憫,乃是人之常情。」
這是今天早上,兩人上山之時,司徒不凡說的佛偈故事,秦弦月記得,卻不買帳,哼道:「你是想說,本姑娘是假慈悲,你才是真慈悲?」她「呸!」了一聲,不屑斥道:「依本姑娘看,大公子雖然盛氣凌人,言行霸道,令人可恨,但與你相比,至少更有情有義,光明磊落!你的狗屁真慈悲,本姑娘看不見!」
司徒不凡不以為意,坦然說道:「你說得沒錯,我與他,就是天底下兩種不同的人。他的確比我更有俠義心腸,若是在江湖上當個俠客,他必能名揚天下。他也比我更有野心,若是在武林中出任一派掌門,必能將門戶發揚光大。」他一頓,臉色一沉,繼續道:「只不過,我與他所爭的,卻是青雲宮!秦女俠,你看不見我的真慈悲,是因為你根本不了解青雲宮代表了什麼!本公子可以斷言,若是由他出任青雲宮主,江湖必亂,武林必衰!」
秦弦月連聲冷笑,無意與他繼續爭辯,突然高舉長風劍,說道:「摘星攬月人難尋,飛御長風上青雲!你若是要爭那宮主大位,長風劍就在此,你為何不取,偏要捨近求遠?」
司徒不凡搖頭嘆道:「秦女俠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司徒不平倘若取得長風劍,的確便能篤定出任宮主。但我若取得長風劍,卻毫無意義。」他悵然長嘆,繼續說道:「我苦心經營了四年,為山九仞,今晚卻功虧一簣,多年心血,化為烏有,可恨呀,可恨!誰能料到,他竟在這關鍵時刻,神功破關第七重?天不助我呀!」
秦弦月譏諷道:「多半上天也鄙視於你!」
司徒不凡聞言,卻不但不氣,反而精神一振,彷彿備受鼓舞,笑道:「言之有理!上天的確有心偏頗於他,但我命由我不由天,本公子要是認命,也不會奮戰至今了。」
秦弦月奇道:「如此說來,你還沒認輸?」
「當然!」司徒不凡點頭,神色變得堅毅如山,說道:「這一層,本公子得謝謝你,幸得有你,拼死從他手中搶回了寶劍。長風劍只要一日不在他手上,本公子便還有反敗為勝的機會!」
秦弦月垂頭思忖了片刻,突然冷笑道:「戲已落幕,小公子的水袖還不願收?」她也不等司徒不凡答話,便接著哼道:「你引我來到這荒山野嶺,就是為了確保長風劍不會落入大公子手中。少假惺惺了,你打算如何謝我?殺人滅口?」
兩人在說的事,一旁郭大膛聽得一知半解,始終搭不上話,但這一句他卻聽明白了,嚇了一跳,驚道:「又要殺人?你們這些江湖中人,怎的殺人比老子宰雞還隨便?難道除了殺人,就沒有別的手段?」
司徒不凡神色變得肅穆,冷冷說道:「本公子也很抱歉,但秦女俠說得沒錯,的確只有死人,才永遠無法洩露長風劍的下落!秦女俠,你既然早已猜到本公子的身份,便不該如此輕率,跟我來到此處。既然來了,那便別想再離開了!」
秦弦月此時倒的確有些後悔,她當時一心想當面揭穿慈悲和尚的把戲,竟忘了顧及安危。她又想起了那神秘艄公的話,也不知該怪他算得不準,還是該怪自己太過輕信,她此行雖已到了目的地,但此處卻不但沒有「活路」、沒有「可以託付終身、長相廝守之人」,反而只有一心要取她性命的大、小二公子。也罷,反正當時在汀河之上時,她便已說過,世上已無叫她留戀之事,倒是害了郭大膛,她有些愧疚,於是說道:「匹夫無罪,懷璧其罪。我既然拿起了這把劍,便早已預料有這一天。我可以留下,放這屠夫走吧!他是無辜的。」
「抱歉,」司徒不凡卻搖頭冷漠道:「本公子不敢冒險,他也不能走。」
郭大膛聞言怒不可遏,喝道:「欺人太甚!依老子看,你這小公子,本事比大公子差多了!你想殺老子,先問過老子的宰刀!」
他話沒說完,刀便已砍了出去。司徒不凡早有提防,不慌不忙,徒手應戰,兩人瞬間交上了手。
司徒不凡的掌法變化多端,靈動詭譎,便像主人一樣,陰險狡詐;而郭大膛的刀法卻直來直往,樸實無華,也像主人一樣,乾脆利落。拙能勝巧,巧能制拙,本來都是對方的剋星,勝負就在於個人的修為。論臨敵經驗、功力深淺,郭大膛都遠不及司徒不凡。三招一過,他見對方掌影幢幢,彷彿來自四面八方,本來只要能穩住心志,一刀劈老,對方的虛招自破,但他的心卻先慌了。司徒不凡看見破綻,虛招轉實,一掌長驅直入。他向來行事果決,既已打算殺人,這一掌便不再留力,掌風凌厲,力道兇猛,「啪!」正中郭大膛胸口。
郭大膛一聲慘叫,身子彈飛丈許,還在半空,便已口吐鮮血,灑作一道赤虹,落地時更已昏迷過去,身子不由自主,竟朝著斷崖滾地而去!秦弦月見狀大驚,情急中也不知哪來的力氣,撐起身子一撲,就在郭大膛滾落斷崖之際,驚險抓住了他一條手臂。
郭大膛昏迷不醒,吊在半空,秦弦月趴在地上,一手緊抱長風劍,一手勉力拉住郭大膛,但重傷無力,似也撐不了多久。司徒不凡不再理會郭大膛,反一手去奪寶劍,喝道:「把劍交出來!」秦弦月不甘就範,左右閃躲,罵道:「你休想!」司徒不凡心下惱怒,目露凶光,狠聲道:「那便先斃了你!」說著高舉肉掌,一掌拍下!
這一掌也毫不留情,灌滿了內力,殺氣騰騰!掌風逼來,秦弦月迫不得已,情急下撒手放開了郭大膛,驚險滾開躲過。司徒不凡一掌拍到地上,掌力激起砂石四射,秦弦月爬起身來,探頭朝斷崖下一望,只見雲霧重重,深不見底,郭大膛身影很快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她從前在弄紅塵裡,也見過娘親殺人,手段也不比司徒不凡仁慈,但目標卻至少有個該死的罪名。像司徒不凡這般,純粹為了一己私利,而視人命如草芥的行徑,連她亦感到一陣不寒而慄。郭大膛與她沒什麼交情,但卻總算在司徒不平手中救了她一命,如此死於非命,她彷彿也間接脫不了關係。她心中怒火陡生,抬頭怒瞪司徒不凡,質問道:「難道憑著『青雲宮』三個字,你便可以肆意殺人,無需理由?」
司徒不凡冷冷說道:「本公子他日當了宮主,不會忘了你們今日的犧牲!」
秦弦月厲聲怒斥道:「在你眼中,天底下就只有兩種人,一種可以被你任意犧牲,另一種,是你自己!」
司徒不凡不想爭論,輕嘆道:「交出長風劍吧,本公子讓你死得痛快!」
秦弦月怒不可遏,突然仰天大笑,厲聲說道:「今日叫你知道,天底下還有第三種人!本姑娘看了你一場戲,如今便還你一折《金沙灘》,演一回楊七郎,即便捨了一條命,也偏不讓你奸計得逞!」
她一句罵完,把心一橫,突然抱著長風劍,一躍而起,竟跳下了山崖之中!她抱劍赴死,倒不是因為捨不得寶劍,只不過既然無論交不交出寶劍,司徒不凡都打算殺人滅口,那便拼著一死,也斷不能讓他稱心如意!
司徒不凡大吃一驚,但事出突然,想要阻止卻已慢了一步。他朝斷崖下一看,秦弦月身影迅速變小,很快便被黑暗吞噬,無影無蹤。他不禁暗暗嘆了口氣,心中不免有些懊悔。他千算萬算,卻竟沒有算到,到了關鍵時刻,秦弦月的性子便如她父母一般,剛烈決絕,寧折不屈!他怔怔沉思了片刻,仰天一嘆,喃喃說道:「罷了,如此也好,你便帶著長風劍,永遠一起消失吧!」
——
秦弦月但覺耳際風聲呼嘯而過,身體似乎無止盡地下落,速度越來越快。她閉上了雙眼,準備好赴死,過往的記憶在腦海迅速閃過,想起了弄紅塵、娘親、還有秦藏鋒。
彷彿過了許久,又彷彿只不過眨眼之間,突然衣領一緊,彷彿一股力量把她拉住,她心中一凜,睜眼一看,不禁大吃一驚。只見一人一手提著她衣襟,另一手扛著郭大膛,在萬丈懸崖山壁上跳躍如飛,如履平地,兩旁景物飛掠而過,速度驚人,竟不比下墮之勢慢多少。這份輕功,已不像是人間所有,而彷彿是仙人在半空之中御風飛行,又如鬼魅自陰司而來拘捕魂魄。
此人身材彷彿很是高大,身披斗篷,面目深埋在黑暗之中,看不清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,很是神秘。秦弦月嚇得哼不出聲,任由他提著飛掠而去,風馳電掣,也不知到底飛了多遠,到了何處,只知他停下之時,人已進入了一處山洞之中,地上還生了一堆篝火。
他放開了秦弦月,又把郭大膛輕輕放在了地上躺好。郭大膛依舊昏迷,嘴角血跡未乾。秦弦月驚魂甫定,此時才看清,地上除了郭大膛,原來還躺著兩人,皆雙目緊閉,也不知是死是活,卻竟然是黎空谷及藍無風!
他們怎會在此?斗篷人又是何方神聖?秦弦月驚駭不已,滿腹疑問,正要開口,那神秘人卻突然朝她眉心隔空屈指一彈,秦弦月但覺一股柔和的力道壓迫而來,突然眼前一黑,竟便已昏迷了過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