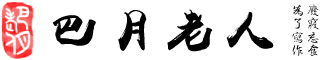花臉獻媚
司徒不平負手而立,仰頭閉目,儼然一副引頸就戮的神態。想起種種舊事,鐵丹怒從心起,按捺不住,突然大喝一聲,一躍而起,一拳衝向司徒不平!
這一拳直截了當,沒有花招,勢如流星,單刀直入。司徒不平既然說了絕不還手,鐵丹便也無需費力打出亂拳。但招式雖然簡單,力道卻不可小覷。拳風迎面襲來,司徒不平卻果然不閃不躲,面不改色。拳頭一馬平川,直打到司徒不平胸口前三寸,鐵丹卻突然停下收力,身子凌空一番,復又退回原地站好,怒喝道:「罷了!用你所傳的招數,打到你身上,這種事我鐵丹幹不出來!」
司徒不平竟反倒略感失望,睜眼勸道:「鐵丹兄弟,你把怨氣積在心裡,對你日後練功,多有不利。若能助你早日解開心結,放下舊日仇恨,這一拳,本公子受得心甘情願。不必顧忌,放馬過來吧!」
鐵丹氣極反笑,譏道:「大公子呀,你這是在求我打你?以往盛氣凌人的氣焰哪去了?看來你為了得到長風劍,還真放得下身段呀!」他一頓,索性袖起了雙手,哼道:「這一拳我鐵丹說不打就不打!但你放心好了,我答應你,投大公子一符,如此,你便該滿意了吧?」
司徒不平相當滿意,一笑抱拳道:「鐵丹兄弟果然坦蕩,本公子佩服。既然如此,本公子便不強人所難了。」他一頓,對秦弦月卻還有些不放心,便又輕嘆一聲,接著道:「兩位,還請務必體諒本公子的用心。舍弟司徒不凡寡情薄義,行事可不如本公子這般講究道義。本公子不忍江湖受其荼毒,不得已才出手阻止他染指長風劍。秦女俠,你在他手上,不也吃了不少苦頭嗎?」
他言下之意,秦弦月自然聽得明白。但她被司徒不平強迫收下了這一份大禮,卻心有不忿,不願當面許諾,只好悶哼說道:「多謝大公子提醒,符條上該怎麼寫,本姑娘自有分寸!」
「好。」司徒不平也不敢太過強硬,便抱拳道:「秦女俠傷勢雖已無大礙,卻仍需多多調息休養,本公子便不打擾了,就此告辭。」
——
秦、鐵二人目送司徒不平離開,各有心思,皆沉默不語。過了良久,鐵丹才突然一笑,說道:「你看起來似乎很糾結。」
秦弦月不否認,氣惱道:「台上兩個小生,皆是混蛋奸角,叫人喝彩都不知該往哪邊喊。他們當中,無論誰得到了長風劍,我心裡都不痛快!」
鐵丹笑道:「但其中一個混蛋把你打下山崖,另一個混蛋卻替你運功療傷。你投桃報李,至少能把人情還清。」
「哦?」秦弦月揚眉質疑道:「你也為司徒不平說情?」
鐵丹搖了搖頭,突然說道:「小公子不久前也來找我了。」
秦弦月忍不住噗哧一笑,嘆道:「這兩個混蛋,平日裡愛唱霸王登殿,目中無人,如今為了一把破劍,倒學起小丑陪笑,一身威風唱成了花臉獻媚,爭相拉攏我等了!」
「那倒不是。」鐵丹笑道:「小公子反而認為,我等六人其實根本左右不了天命燈的兆象。」
「此話何意?」
鐵丹忍不住學著司徒不凡的神情,故作神秘,答道:「好問題。」他自然也沒有答案,一頓後又接著道:「我只是想告訴你,你其實不必糾結,大可放心投大公子一符。」
秦弦月不忿道:「可你我兩人,再加上郭大膛,他便已掌握至少三符了!」
「不對。」鐵丹眼中閃過一絲狡黠,低聲說道:「我的符條上,將會寫一個『小』字。」
秦弦月眨了眨眼,奇道:「你明目張膽,對司徒不平撒謊?」
鐵丹失笑道:「像你我這種人,撒個謊何足為道?但還是錯了,我方才並沒有撒謊。」
秦弦月聽他將兩人相提並論,本想反駁,但轉念一想,自己也的確欺騙過不少人,只好把話吞了回去。鐵丹繼續說道:「我答應投他一符,說到做到,只不過這一符,在昨晚便已經投了!」他一頓,輕嘆一聲,接著解釋道:「我在他面前雖然嘴硬,但他說得對,我一身武功都是他所傳,昨晚投他一符,便是為了還清恩情,此後再無拖欠!」
他方才懸崖勒馬,臨陣收回一拳,便是為此。他突然想明白了,那一拳倘若打了下去,那三天後符條上,便不得不寫上大公子了,但他卻心知肚明,兩人武功差距太大,那一拳雖然解恨,但對司徒不平而言,卻不痛不癢,所能造成的傷害,遠不比把符條投給小公子來得大。
秦弦月掩嘴譏笑道:「沒看出來,你倒也恩怨分明!」
鐵丹不以為意,反而嘆道:「欠人恩情的滋味不好受,所以我勸你,還是也儘早還清。你我兩符,一大一小,正好抵消,長風劍的歸屬,便讓那見鬼的天命燈自行決斷吧!」
秦弦月沉思片刻,皺眉懷疑道:「一個發霉壞掉、又沾了臭醬的皮蛋,能吃下肚嗎?」
鐵丹苦笑道:「鹹月餅,我前日戲弄了你,但你也淋了我一身糞水,兩廂總該扯平了吧?如今山莊暗流湧動,你我更應該化敵為友,守望相助,你說呢?」
秦弦月本就不想蹚這渾水,昨晚她符條上,寫的就是一個「秦」字,等同棄權。鐵丹的提議,正合她心意,她想了想,拿定了主意,抬頭說道:「好,本姑娘便再信你一次。你我兩符,一大一小,相互抵消,一言為定!」
——
司徒不平為秦弦月療傷,表面上不費吹灰之力,但其實耗損不小。離開之後,他不得不回到自己廂房,運氣調息了半天,才總算恢復了元氣。窗外天色依舊漆黑一片,但他卻心裡清楚,如今應該已近日落時分了。
他在心中默默數了一遍,郭大膛、鐵丹、秦弦月,這三符到手,便已立於不敗之地。藍無風對她怨念太深,這一符只怕已無法挽回。剩下雲菲語、小勺子,這兩人與白行舟、何長嘯有些淵源,眼下是仇,但說不定也可以化為情,一婦一孺,皆沒多大見識,應當不難處理。這兩符再弄到手,兩天以後便穩操勝券了。
想到此處,他心情大好,離開了院子,打算先去見一見雲菲語。
來到雲菲語的院子,內裡卻不見人影。不遠處傳來人聲,司徒不平循聲尋去,來到下人平日做飯的廚院。聽院裡聲音,雲菲語果然在此,除了她,還有小勺子、以及郭大膛。
司徒不平突然想起,昨日郭大膛叫了一聲「菲語妹子」,心中一動,施展輕功,縱身跳上了屋頂,悄悄接近,暗中窺探。
時候已不早了,山莊裡再無下人侍候,眾人一日三餐,總不能只啃那乾燥無味的乾糧。小勺子首先抱怨,拉著雲菲語去廚院弄些好吃的。廚院裡不但爐灶鍋勺具備、新鮮食材充足,柴米油鹽醬醋茶亦樣樣齊全,兩人見狀,便準備下手做幾道佳餚。小勺子從前家裡開客棧,對廚房雜活還算熟悉;雲菲語打小自力更生,燒幾盤小菜也不成問題。兩人有說有笑,便幹起了活。
這時郭大膛聞見聲響,也趕來湊熱鬧。見了兩人,愣頭愣腦笑了笑道:「小勺子、菲語妹子,做飯呢?我也搭把手吧?」
雲菲語抬頭瞪了他一眼,卻板起了臉,冷淡說道:「你若餓了,多做你一份便是,請別來添亂。」
郭大膛只知傻笑,倒是小勺子打圓場道:「怎麼會呢?我聽說了,大湯鍋可是個經驗老到的廚子,手藝不凡,連大公子都讚不絕口,有他幫忙,自然更好。大湯鍋,快來、快來。」
郭大膛自打來到山莊,第一眼看見雲菲語,便忽覺恍如夏日仰躺在柔軟的青草地上,沐浴著溫暖的晨陽,鼻下彷彿還能聞到淡淡清新草香,瞬間神魂顛倒、一見鍾情。他年近三十,卻尚未婚配,二十歲那年,父親本來正打算為他說一門親事,卻突然因病身故,此事便耽擱了下來。父親死後,他獨力打理肉館,也沒去多想自己的終身大事,直到如今遇上這一位江南嬌娘,才忽感怦然心動,難以自禁。
只不過雲菲語才剛從白行舟指下死裡逃生,如今看見郭大膛色瞇瞇的猥瑣模樣,卻只覺厭煩難耐,對他始終冷淡疏離,避之不及。小勺子及鐵丹看熱鬧不嫌事大,反而多次想方設法撮合。他們知道雲菲語才剛經歷了白行舟之痛,也知道雲菲語表面上強顏歡笑,其實心裡卻還未放下往事,兩人都一致主張,想要療愈情傷,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找個新的情人。
雲菲語初到山莊時,想起前事,不禁心如槁木,萬念俱灰。可嘆因果輪迴,報應不爽,此時終於體會到當初在月老廟,白行舟得知自己給他下毒時的心情。白行舟最後狠下殺手,但她卻狠不下心腸責怪情郎,只覺羞愧難當,無地自容。在山莊休養,身子一日日康復,心情卻越發萎靡,幸得小勺子常找她說話,多方開導,才熬了過來。小勺子父母雙亡,也覺孤苦無依,雖有一個鐵大哥處處關照,卻還覺不夠,後來乾脆也認了雲菲語作乾姊姊。多得有了這個乾弟弟,雲菲語心中有了寄託,才逐漸重新振作起來。
看明白郭大膛的心意後,小勺子便私下遊說雲菲語,何不也考慮一下?雲菲語紅著臉斥道:「乳臭未乾,沒大沒小!」小勺子笑道:「姊姊莫欺我年少,男女情愛,不過就那麼回事,弟弟我也不是沒經驗!姊姊說過,一生所求,不過是過些平凡安穩的日子,那就得找個老實男人,尤其不能找鐵大哥那種,他雖然專情,人卻太狡猾了,姊姊治不住他。弟弟看得出來,那大湯鍋就是個老實人!雖然盯著姊姊看時醜態百出,但卻正說明他藏不住心事,憨厚樸實啊。」
他滔滔不絕,道理雖在,但一個來自漠北的小男孩,又怎知一個江南姑娘的心境?莫說郭大膛五大三粗、不解風情,與雲菲語以往所求,大不相同,只說白行舟逝世不久,此時便談兒女私情,豈非太也無情放蕩、水性楊花?
鐵丹也沒閒著。一個女子對你感到厭煩甚至敵視,如何打動她的芳心,鐵丹在這一方面,正巧有些經驗。當年夜夜潛入憐兒宅院,所用的手段,其精神內核,是八個字:「精誠所至,金石為開。」其具體行動,也是八個字:「死不要臉,軟磨硬泡。」他把箇中種種要訣,向郭大膛傾囊相授,郭大膛也算「孺子可教」,馬上便悟出了道理,恍然道:「懂了,好比熬湯,小火慢燉,時間就是火候呀。」
郭大膛拿定了主意,從此便天天糾纏,逗雲菲語說話,不管雲菲語如何冷待,也還是一口一句「菲語妹子」地叫著。如今山莊雖然發生了異變,但自然也還是攔不住他,更何況,此時一旁還有小勺子幫襯著說好話。雲菲語生性柔婉,向來待人接物總留三分情面,即使心裡不痛快,也不忍把話說絕。只是這些天來著實被郭大膛死皮賴臉惹得急了,此時才冷言冷語說了一句「別添亂」,但卻也已是極限了。
做飯燒菜正是郭大膛的拿手好戲,正好趁機賣弄一番。他重操舊業,一拿起菜刀,眼中便閃現出光芒,彷彿變了個人,更彷彿忘了身上傷勢,精神大振,甚至有點英明神武。他起灶燒鍋,殺雞起骨,手法駕輕就熟,乾脆利落;他刀起如風,行雲流水,蔥段齊如兵列,肉片薄如蟬翼。他打小長於山東,卻知道江南人偏愛清淡鮮甜,於是放棄了最拿手的「蔥爆雞丁」,改做一道「西湖醋溜雞片」。鍋中清油微熱,雞片在油中翻身如白鶴展翅,黃酒、陳醋、冰糖、醬油在慢火中交融,轉瞬間滿室生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