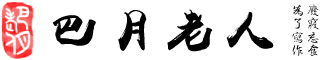授藝施恩
「大公子?」也不知司徒不平是何時來到,看了小勺子忘我起舞多久,小勺子耳根一紅,略感惱羞,慍哼道:「你別欺我年少,江湖規矩,我還是知道一些。偷看別人練功,是很無禮的江湖大忌!」
「練功?」司徒不平強忍住笑意,說道:「好,算本公子一時莽撞,本公子在此,便給小友賠禮道歉。」
他話雖客氣,語氣卻帶著不屑。小勺子氣不過,悶哼一聲,正要轉身離開,司徒不平卻又悠悠說道:「本公子看小友骨骼清奇,倒不失為一個習武的好苗子,小友若是想學劍法,本公子說不定能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小勺子不由得頓住了腳步,回頭問道:「你為何要幫我?」
司徒不平輕輕一嘆,答道:「本公子知道,你爹娘之死,雖說全是司徒不凡在幕後興風作浪、挑撥離間所致,但我那手下何長嘯,也有識人不明、辦事不力之責。你爹趙切趙大俠,也是本公子非常敬重之人。勺子小友若不嫌棄,本公子可以傳你一套劍法,只算是提攜故人之後,聊表敬意。」
小勺子聞言忍不住放聲大笑,說道:「鐵大哥提醒過我,說大公子你早晚會找上我,果然說中了。你客客氣氣,對我巴結奉承,說到底,也只不過是看上了我手上一張符條罷了!」
司徒不平當然正是這般心思,遭當面說破,亦不動氣,只淡淡笑道:「本公子與司徒不凡之間,你總得作個選擇。本公子此舉,只不過是想讓你更容易作出決定罷了。」
小勺子想了想,眼珠一轉,計上心頭,便抬頭道:「也罷,要我跟你學,也不是不可能,但你且先說說,你的劍法,叫什麼名堂?有什麼厲害之處?」
司徒不平笑道:「厲害的劍法本公子有的是,只不過,勺子小友,習武可不能一蹴而就,你沒有武功底子,太上乘的劍法,你也學不來。我傳你一套『七絕劍』,七劍連環,招招狠辣,講究一擊必殺,而且練起來難度不大,於你最為合適。」
「呸!」小勺子皺眉猛搖頭道:「這名字忒不吉利!我才十四歲,你就要我『七絕』?這不是咒我早死嗎?不學、不學!」
司徒不平微一沉吟,又道:「有一套『青蓮君子劍』,劍法端方清雅,如君子立世,出招正大光明,毫無陰險詭計。這名字,總算吉利了吧?」
小勺子還是一臉嫌棄,說道:「君子?我小勺子從來不稀罕當什麼君子,我要學了這劍法,日後江湖上保不齊給我取個外號叫『小君子』,聽著就犯噁心!不學、不學!」
司徒不平強忍著怒氣,又道:「還有一套『霜寒十三式』,一劍一寒意,劍到之處,寒霜遍地。你若練成,也能躋身武林,成一號人物了。」
小勺子聞言忽地打了個冷顫,連連搖手道:「不成不成,大公子呀,你是存心想害我吧?我這人出身大漠,挨慣了炎熱,偏偏就是怕冷。練了這劍法,還不得整日打哆嗦?劍還沒出鞘,我先凍死了!不學、不學!」
連番無理推搪,司徒不平總算明白被小勺子戲弄了,忍不住動怒,臉色一沉,冷聲斥道:「臭小子,不識抬舉!」
小勺子笑道:「這就發怒了?好、好、好,我明白告訴你吧,我別的都不學,就只要學一套,霄山派的凌霄劍法!」
司徒不平一怔,冷笑道:「霄山派的劍法,稀鬆平常,有何稀罕?即便練至巔峰,也難稱雄武林!」
小勺子聽他詆毀娘親的劍法,心下更為不悅,哼道:「不必多言,你倒是會不會?若是會,我便考慮跟你學;倘若不會,那便多說無益,明天晚上,我符條上寫上小公子便是了!」
青雲宮的藏書閣裡,收藏了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學典籍,凌霄劍法能得七弦劍仙秦藏鋒評一句「湊合還過得去」,也算享譽武林,自然也在其中。只可惜,學海無涯,人力卻有限,這一套劍法,偏偏司徒不平就不曾練過。他一時無計可施,只好沉聲責問道:「司徒不凡害死你爹娘,你偏要認賊作父?」
「呸!」提起爹娘,小勺子怒氣又起,反駁斥道:「貓哭耗子假慈悲,你三言兩語,便想與惡霸何長嘯撇清關係、把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,我才不上當!」
司徒不平老羞成怒,氣極冷笑道:「小兔崽子,你是否有一件事算錯了?」
「哦?」
司徒不平臉色變得陰沉,繼續冷聲說道:「你以為本公子有求與你,便不敢對你動手,只不過,你倘若執意要站在司徒不凡那一邊,那你活著,對本公子便是弊大於利了!」
司徒不平以俠士自居,生平的確從不曾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孩子下過毒手,不過長風劍事關重大,這一刻,他似乎已決定破例一次。他的神色變得冷峻,目露凶光,四周彷彿瞬間飄起一股殺氣,直逼小勺子眉心。小勺子不由自主打了個冷顫,被這一股莫名的氣勢壓得透不過氣,頓時冷汗直流,心中叫苦,喉嚨卻竟發不出半點聲音。
司徒不平若要取小勺子性命,只怕連手指頭也不必抬,生死只在一念之間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,空中突然響起一陣竹笛樂聲。笛聲悠揚洪亮,曲調輕快歡暢,竟把現場殺氣消弭大半。小勺子頓感壓力大減,司徒不平亦暗暗一驚,轉頭一看,一人衣袂輕飄,橫吹竹笛,從花叢中徐步走來,正是秦弦月。
虎父無犬女,秦弦月家學淵源,在音律樂理上本就極富天份,加上數月以來的修練,此時吹出的曲調,與當日初學時相比,已有天壤之別。她閉目吹笛,彷彿渾然忘我,直走到兩人身前不遠,才放下竹笛,微笑說道:「抱歉,本姑娘不知此處有人,竟忘情獻醜了,但願沒有驚擾了大公子。」
司徒不平收起了怒容,嘴角擠出一絲笑意,淡淡道:「怎麼會呢?秦女俠的笛聲,正好為這孤寂的山莊,添一份歡樂意興。」
秦弦月的曲調意境再高,也不可能壓得住司徒不平。司徒不平此時退讓,原因之一,自然還是因為心中對七弦劍仙還存有三分敬畏,而這也正是秦弦月以笛聲現身的用意。此時她見計策湊效,便又再問道:「大公子方才大動肝火,難道是這孩子不懂事,又冒犯了大公子?」
話說得婉轉,卻有意大事化小,言下之意,是表明了立場,要保下小勺子了。司徒不平心中暗忖,早前耗損了不少元氣拉攏秦弦月,此時倘若翻臉,豈不前功盡棄?當下哈哈一笑,一揮手說道:「一場誤會罷了,本公子又怎會與一個孩子一般見識?」
秦弦月也笑道:「那是,大公子若是沒有《打龍袍》裡仁宗容包公之肚量,又焉值得本姑娘手上一張符條?」
這句話乍一聽來,像是一種威脅,但同時卻又是一種表態。秦弦月早前不肯當面答應站在司徒不平這一邊,但此時卻顯然暗示了這一層意思。司徒不平聽明白了,不禁心下大悅,怒氣全消。他暗暗盤算,自覺已是勝券在握,小勺子手上的符條,反而已無關緊要,留他一命,亦無損大局,於是一笑說道:「秦女俠是性情中人,深明大義,甚合本公子之意。」他一頓,又笑著嘆了一聲,接著道:「勺子小友,本公子為你感到惋惜呀。江湖上多少人,求本公子指點一招半式而不得,你一念之差,便錯身而過。罷了,你我無緣,不可強求,好自為之吧!」
他一邊說著,一邊轉身離開,步履看似悠然,但一句話說完,人卻已不見了影蹤。秦弦月這才暗裡鬆了口氣,回頭瞪了小勺子一眼,語帶責備道:「小勺子,你膽子也太大了!」
小勺子驚魂甫定,心裡也知道自己玩過了火,但嘴上卻不肯認輸,悶哼一聲喃喃道:「大不了殺了我,我也早日與爹娘在黃泉相聚!」
秦弦月聞言一怔,竟感同身受,頷首悵然道:「我爹娘也一樣雙雙離世,我也曾想過自尋短見,追隨他們。」
小勺子見狀,反倒暗吃一驚,忙道:「秦姊姊可千萬不可有此想法!我方才不過一句氣話,爹爹臨終叮囑,要我好好活著,我還得學劍法、還得娶媳婦,還想活到八十,天天吃肉呢!」
秦弦月暗叫一聲「慚愧」,甩了甩頭,回過神來,問道:「司徒不平人雖可惡,卻說得沒錯,你若想要習武,為何偏要推卻這天賜良機?」
小勺子哼道:「誰說我要習武了?武功是害人之物,我才不學,我只不過是想學霄山派的凌霄劍法罷了。」
「哦?」秦弦月不解,「那是為何?」
小勺子道:「這是娘親生前所用的劍法,我要是學會了,那便宛如娘親常伴左右了。」
秦弦月又一怔,不由得反思自省,幽幽說了一句:「的確如此。」
回想自己近來勤練竹笛,豈非也是同理?她自小父親便不在身邊,娘親性情孤僻,對她亦是若即若離,與秦藏鋒相處的日子雖然不長,但父女之情其實卻已暗暗紮根,豈料後來才剛相認,卻又是天人永隔,除了一把竹笛、一門劍法,再也沒留下其他。
他的心思,小勺子自然不懂。他接著說道:「大公子教不教,本就無所謂。我早打聽過了,霄山雖然遠在湖北,萬里迢迢,不過公孫先生答應了,待此間事情了結之後,便送我去霄山。只要見到了霄山掌門,我自有辦法讓他教我。」
「哦?」秦弦月被他的話引起了興趣,抽離哀思,笑著好奇問道:「我聽說霄山派收徒極嚴,你一個孩子,有何能耐叫霄山掌門聽你的?」
小勺子遲疑了片刻,才說道:「也罷,秦姊姊不計較前番『落井下屎』之嫌,仗義相救,我不該有所隱瞞。」說著,他從懷裡取出一團破布,那是他從當日逃離荒城寨時,身上所穿衣物撕下的布塊。他小心翼翼打開布團,裡面包裹之物只有指頭大小,秦弦月湊近一看,那事物平凡之極,但她卻心頭一驚,脫口說道:「一枚琴軫?」
小勺子對琴軫珍重之極,急忙又包好收回,說道:「這可不是一枚普通的琴軫!這是一位高人所贈,他說了,霄山掌門只要見此信物,必能助我!」
「高人?」秦弦月心中其實已有答案,卻還是忍不住問道:「何方高人?」
小勺子神秘笑道:「巧了,這位高人與姊姊一樣,姓秦!」
他神秘兮兮,吹噓起秦藏鋒在荒城寨的事蹟,如何一撥琴弦,便讓人動彈不得。秦弦月自然早已知道父親的本事,但從外人口中聽來,卻依舊心生嚮往,與有榮焉,她也沒有想到,原來秦藏鋒與小勺子還有如此一段淵源。等小勺子吹噓完了,她才點頭笑道:「有這一枚琴軫,莫說霄山掌門,只怕連少林方丈、太乙觀主,也得聽你的。」她一頓,又輕輕一嘆道:「只不過,那公孫聞道為人神神叨叨,未必可信。你也別指望他了,你我倘若果然能夠活著離開此地,我親自帶你去霄山。」
既然是父親的意思,她自忖似也該盡一份力。小勺子聞言大喜,但又奇道:「秦姊姊的口氣,似乎有些悲觀?過了明晚,禁法自解,難道還會有意外?」
他畢竟年輕,思慮有欠深遠,秦弦月苦笑道:「司徒不凡雖然說得信誓旦旦,但他自己也身在局中,眼前處境詭譎難測,又有誰能說得準?」
小勺子怔了片刻,又豁然笑道:「無論如何,至少在明晚祈燈大會之前,大夥應該都是安全的吧?這一段時間,也已足夠做很多有趣的事了!」
秦弦月見他眼中閃起了狡黠的光芒,忍不住問道:「你這小鬼頭,又想到什麼鬼主意了?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