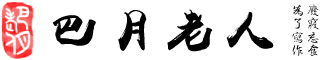忽見斗篷
小勺子掩嘴竊笑,眼珠亂轉,顯然不懷好意。他裝模作樣,嘆了口氣道:「本來該幫大公子,還是小公子,我也難以抉擇。不過方才受了一番驚嚇,想來符條上,是鐵定不能寫大公子了。只不過倘若如此輕易便站到小公子這一邊,便宜了他,又著實不甘心。」他嘿嘿一笑,接著道:「秦姊姊,你與小公子也有些過節吧?我們何不聯手,也來給小公子設一局『落井下屎』,解解氣?」
秦弦月失笑氣道:「這頭才得罪了司徒不平,那頭便又要去招惹司徒不凡?」
小勺子笑道:「鐵大哥說過,柿子撿軟的捏,咱惹不起大公子,難道還惹不起小公子?他要是耍起狠來,咱便往大公子處逃,有大公子撐腰,小公子又還能掀得起什麼浪來?」
聽起來荒唐,但秦弦月卻竟怦然心動,幾乎便要被說服了。一盆子糞水穢物,扣到司徒不凡的光頭上,還要叫他發不出脾氣來,這個念頭確實誘人,想想也有點小激動,她忍不住噗哧一笑,竟追問道:「計將安出?」
小勺子卻沉吟道:「若要成事,還得叫上鐵大哥!」
秦弦月臉色一變,哼道:「又是那個臭皮蛋!」
小勺子笑道:「鐵大哥還說過,君子怕小人,小人怕痞子。小公子人雖可恨,卻狡詐多疑,他的手下東方九冬已是如此難纏,要對付他,還真就得拉鐵大哥這臭皮蛋入夥。」
秦弦月不買帳,冷笑道:「他有何能耐?上一次想算計本姑娘,最後還不是自己吃了虧?」
若論設局騙人,她堂堂弄紅塵大詞人,自忖本事絲毫不會輸於一個臭痞子。不過小勺子卻似有異議,他欲言又止,還掩著嘴強忍笑意,彷彿秦弦月的話,滑稽可笑。秦弦月看在眼裡,不是味道,沉臉慍道:「有話便說,別吞吞吐吐!」
小勺子這才笑著嘆道:「罷了,既然事情已然過去,我也不怕對秦姊姊坦白。當天那一局『落井下屎』,其實一切都在鐵大哥預料之中。鐵大哥被你拉落井底,是有意為之,那便桶裡裝的,根本不是什麼糞水穢物,只不過是泥巴混了濃茶。鐵大哥這一局,目的並非要陷害秦姊姊,而是要打破你與雲姊姊之間的隔閡,助你二人化解恩怨罷了。而後來你二人也確實和好如初了,可見這一局,鐵大哥是料事如神,大獲全勝呀!」
秦弦月得知了真相,不由得陷入了沉思,臉上陰晴不定,似有怒意,又似有羞愧,一邊惱火中人圈套,一邊又確實慶幸與雲菲語冰釋前嫌。過了良久,她才長長嘆了一口氣,冷冷一笑,哼道:「本以為是《十五貫》裡的婁阿鼠,卻原來湊合也有幾分《白兔記》裡劉智遠的味道。既然如此,便不妨與他再合唱一場,且看這一齣,是《單刀會》,還是《西廂記》?」
小勺子雖也隨鐵丹逛過幾次戲園子,但這一番話的意思,他卻聽不明白。他一臉迷茫,秦弦月卻沒有要解釋的意思。有時候,有些話,就是要說得晦澀難明,才是目的。
——
司徒不凡想通了心中苦思多時的疑難,心情大好。心情好,時間彷彿過得也快些,不知不覺,困在山莊里的第二天便已過去,根據漏壺上的刻度,太陽應該也已下山了。
這一晚,司徒不凡乖乖躺在床上,準備入睡。他不打算再去監視小千山莊,他知道,即便目不轉睛盯死了,他還是會身不由主地打盹,一眨眼便是天亮。不該他看的事,他絕對看不見。至於天亮以後,小千山莊又會發生什麼變化,他也已心中有數。今日的大千山莊,會變成明日的小千山莊,今日的小千山莊,會變成明日的小小千山莊,這一層,已不必再多作證明。
合上眼,他想起明日晚上,便又是問命大會了。與司徒不平不同,他對此毫無緊張之感。他已猜透了「天」意,已然預料到了問命的結果,他只是很好奇,當結果公佈之時,這一座詭異的大千山莊,又會發生什麼變化。
這一晚他睡得很好,山莊裡的高床軟枕,絕對不比青雲宮差。他睡到自然醒來,悠閒地梳洗整齊,戴好頭巾,獨自坐在院子中,倒了一杯茶,輕輕品賞,心中默默數了數時辰,應該也已是辰初前後了吧。
正感愜意,突然院子外傳來一陣尖叫聲,驚得他抖灑了半杯好茶。
「你意欲何為?把人放下!」是秦弦月的聲音。
接著「嘭!」一聲巨響,院子大門被猛力撞開,一個人影倒射而入,跌倒在地上,正是秦弦月。
秦弦月掙扎著爬起身來,模樣狼狽,似乎摔得不輕。司徒不凡面不改色,動也不動,一手仍舉著半杯茶,一笑招呼道:「你也起得早呀,秦女俠!」
秦弦月神色著急,只抬頭瞪了他一眼,也不回話,便匆忙拔腿又追了出門,喊道:「放了小勺子!」
司徒不凡還是不動,好整以暇,徐徐喝完了茶,才輕嘆了一聲,身子突然彈起,疾射而出,追了上去。
他並不擔心秦弦月的安危,不過在他的推演當中,在今晚問命大會之前,山莊里卻不應該會出什麼意外。聰明的人,往往都忍不住好奇心。
秦弦月施展輕功,躥房越脊,司徒不凡也飛簷走壁,遠遠跟著。沒跑多遠,秦弦月突然在一所房子屋頂上停下,蹲下撿起一件事物,怔怔發楞。司徒不凡正好追上,從她身後一看,原來是一隻布鞋。
秦弦月喃喃自言自語道:「是小勺子的布鞋,方向沒錯!」
司徒不凡見她神色凝重,忍不住微微一笑,悠悠說道:「司徒不平抓了小勺子,多半也只不過是為了今晚的問命大會罷了,沒有性命之虞,何必緊張?」
「司徒不平?」秦弦月滿臉狐疑,大惑不解。
司徒不凡笑道:「除了他,還能是誰?」
秦弦月搖頭沉聲道:「不,不是他!是那救我一命的斗篷人!」
話音未落,她腳一蹬,無暇理會司徒不凡,又已追了出去。「斗篷人」三個字,宛如三記洪亮鐘聲,震得司徒不凡心頭一顫,目光頓時大盛。「他」怎會現身?不可能!他只怔了片刻,馬上便又拔腿追了上去。事已至此,無論如何,他也得一探究竟。
兩人一前一後,直奔出了人園,衝進了地園假花園中,來到一片空曠沙地,眼前不遠,一棵假樹上吊著一盞燈籠,微弱火光下,只見樹下不遠,果然有一人,身披玄色斗篷,一手扣著小勺子咽喉,高高舉於空中。此人身材高大,面目藏於黑暗之中,根本看不出是老是少、是男是女。秦弦月見狀大急,怒吒一聲:「果然在此!還不放人?」說著手在腰間一抽,軟劍出鞘,抖如靈蛇,腳下不作停頓,一劍便朝斗篷人攻了過去。
斗篷人微微一側頭,也不見他有任何動作,秦弦月卻突然彷彿撞上了一堵鐵牆,一聲慘叫,身子倒彈而去,跌落丈許開外。她咬牙爬了起身,挺劍又再一衝,這一次司徒不凡瞪大了眼,看出了端倪,那斗篷人看似一動不動,但長長垂下的衣袖,卻彷彿一陣清風吹過,輕輕抖了一下。這輕輕一抖,卻似刮起了一股無形掌風,疾射而出,正中秦弦月。秦弦月又悶哼一聲,身子再次彈飛,「哇!」地一聲,噴出一口鮮血,在半空中畫出一道紅橋。
司徒不凡渾身一震,心裡忍不住驚叫了一聲:「碧空拂雲掌!」這一門絕學,他曾經見過,袖裡藏勁,隔空傷敵,威力所向披靡,連司徒不平也還未練得來。
秦弦月倒地,臉色蒼白,搖搖晃晃又再爬起,抖擻軟劍,似乎還要再上。司徒不凡忍不住脫口叫道:「住手!此人若出全力,你早死八遍了,還看不出來嗎?」
秦弦月咬牙切齒,厲聲喝道:「本姑娘偏就不信這邪!」
她彷彿已失了理智,第三次衝向斗篷人。斗篷人顯然不耐煩了,突然掌力一吐,遠遠拋開了小勺子,這才回過身來,雙掌齊出,拍向秦弦月。雖然依舊看不見面目,但卻連司徒不凡也彷彿能感覺到殺氣騰騰,斗篷人這是決意一招徹底解決這糾纏不休的蒼蠅了。
司徒不凡大驚,叫了一聲:「掌下留人!」腳一蹬,一衝上前,想要攔下秦弦月。他身法極快,但衝到近前,卻猛然想起一件事,頓時懊悔。以斗篷人的武功,倘若真要取秦弦月性命,根本無需出全力,一根指頭足矣,何必拋下小勺子?不對,這是個圈套!
說時遲,那時快,念頭方起,忽覺腳下一空,地上沙土竟突然陷落。他大吃一驚,卻臨危不亂,忙提氣一縱,身子陡然拔起,想要跳離戰場。不過這一反應顯然也早已在敵人預料之中。秦弦月神色變了,不再咬牙切齒,卻變得狡黠得意,突然倒戈相向,軟劍迴旋一掃,把他的退路盡數封死。同一時間,斗篷人也不閒著,雙掌化成了流星般的亂拳,朝司徒不凡猛砸而去。他雙臂揮舞,扯脫了斗篷頭蓋,總算露出了面目。此人濃眉大眼,目光如星,太陽穴上還有一道淡血色的月牙疤,正歪著嘴竊笑,更添幾分邪氣,當然正是鐵丹。
司徒不凡身在半空,退無可退,情急之下只能回掌招架這一陣亂拳。但鐵丹的目的不在傷敵,而只是要把人逼回到地上。司徒不凡身不由主,頓時下墜,「噗通」一聲,便已掉進了地下陷阱坑中。但覺鼻下湧來一股惡臭,原來這陷阱坑也只不過四五尺深,但坑里卻填滿了糞水穢物,名副其實一個糞坑,頓時把司徒不凡泡了個渾身濕透。
鐵丹及秦弦月見計謀得逞,停下手來,掩著口鼻退開數尺,捧腹大笑。小勺子也走了過來,更是笑得滿地打滾,停不下來。三人同台出演的一場戲,大功告成,圓滿結局,自然欣喜振奮。不過現場卻竟然還有第四把笑聲。司徒不凡竟也在大笑,他笑著爬了出坑,笑得前仰後合,彷彿絲毫不覺難堪,更絲毫不嫌惡臭,彷彿笑得比其他三人都更要開懷。
秦弦月忍不住停下問道:「司徒不凡,你在笑什麼?」
司徒不凡答道:「我當然該笑。我中了你們的圈套,但你們的陷阱裡,藏的不是刀劍槍戟,而只不過是一池糞泥。本公子大難不死,難道不該笑?」
鐵丹不由得莞爾道:「該笑歸該笑,但我鐵丹行走江湖這麼多年,如小公子這般,沾了一身糞,卻還能笑得如此開懷之人,卻絕無僅有,從未遇過,鐵丹佩服、佩服!」
「好說、好說。」司徒不凡拖著一身濕漉,卻還不忘抱拳還禮,又笑道:「你們三人,為了設此陷阱,也花了不少功夫,過程中要填滿這一池糞泥,想必自身也沾了不少。想到此處,本公子又如何笑不出來?」
這一個糞坑陷阱,挖坑不難,但三人為了填滿這一池糞泥,卻著實費了不少功夫。為了收集更多材料,三人更耐住性子,又多等了一個晚上,一大早到各人住處收羅了所有便桶,最後才有此規模。但辛勞總算沒有白費,秦弦月無怨無悔,笑道:「只要能讓你中計,本姑娘覺得值!司徒不凡,你在龍山設圈套賺我,這一池糞泥,只算是小懲大誡,也為雪球出一口惡氣!」
司徒不凡還是不動氣,反而更顯開懷,喜道:「只要能讓各位解氣,本公子沾沾屎糞,又何足為惜?此計佈局嚴謹,利用了本公子對斗篷人的好奇,節奏更是緊湊,讓本公子全無思考的時間,不愧名家高招。本公子有幸參與其中,著實與有榮焉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