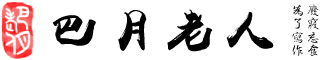獻祭人選
很多年以前,青雲宮裡有一名鑄劍大師,傾畢生所學,研製了兩種助燃物質,一種名叫「陽炎砂」,一種名叫「幽燼粉」,一陰一陽,投入爐中,能調節火勢冷熱,對冶煉各種金屬鐵器,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萬沒想到,多年以後,公孫聞道竟利用了這一點,巧妙地操控天命燈的兆象。
兩片符紙,一片觸感粗糙,氣嗆而味酸,正是抹上了「陽炎砂」;另一片觸感絲滑,氣香而味鹹,正是抹上了「幽燼粉」。這兩種物質,才是真正使天命燈展現不同兆象的關鍵所在。
當然,這天命燈的機關也是鬼斧神工,極盡巧思。燈壁之內其實有多層皮影,每層單獨而言,毫無意義,但多層配合之下,卻不但能在燈壁上構出「兆象」,更能通過調節每層皮影轉角之差,呈現不同的影像,具體而言,天命燈可以呈現四種影像,即此前見過的「八駿圖」、「虎嘯山林」、「龍騰九天」以及「龍虎相爭」。
尋常走馬燈皮影轉動,乃因燈火燒熱燈腹,造成熱氣溢出,氣流帶動燈頂風輪所致。天命燈原理相同,但卻又複雜百倍,有多口風輪,每口各自帶動不同的皮影層。簡而言之,調節燈火冷熱,便能調節不同風輪的快慢,從而又改變皮影層之間的轉角差距,最後便呈現出不同影像。
倘若投入抹了「陽炎砂」的符條,燈火升溫,兆象便是「龍騰九天」;倘若投入抹了「幽燼粉」的符條,燈火降溫,兆象便是「虎嘯山林」。公孫聞道派發給有緣人的五張符條上,顯然有兩張「陽炎砂」,兩張「幽燼粉」,最後一張卻是空符。如此陰陽抵消之下,兆象便是「龍虎相爭」了。
換言之,無論五人怎麼寫,問命結果早已注定。
鐵丹與秦弦月,正好各得了一張不同的符條,機緣巧合之下,這巧妙至極的把戲,便被司徒不凡一眼看破了。這其中的奧妙,司徒不凡雖然一時之間,未必能盡數破解,但其中關鍵,卻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了。當然,他能有此結論,也不盡然是「運氣好些」這麼簡單。若不是出身青雲宮,見識廣博,又怎可能認識「陽炎砂」及「幽燼粉」這等罕見物質?
這時他把心中的推斷娓娓道來,最後感嘆道:「縱然是騙人的把戲,但那天命燈的機關如此精細,也算是一件巧奪天工的寶貝了,可惜呀,被司徒不平一掌打碎。公孫世叔為了設這一局,還真是下了血本啊!」
鐵、秦二人聽得嘖嘖稱奇,膛目結舌,世上竟有如此精巧的機關,著實叫人大開眼界。驚嘆過後,鐵丹莞爾笑道:「如此說來,天命燈果然造假,大公子蒙對了。」
秦弦月也回過了神來,說道:「雖然總算弄明白了天命燈,可這並沒有解決大公子要抓人獻祭的問題。」
司徒不凡正沉浸在恍然大悟的喜悅當中,聞言只好強行把思緒拉回到現實,一攤手嘆道:「這個問題,無解!」
秦弦月臉一沉諷道:「詭計多端如你,怎會沒有辦法?」
「正確的說法,是足智多謀。」司徒不凡糾正了誤會,又聳聳肩道:「即便你們能躲得過司徒不平,也躲不過神龍,所以沒有辦法。」
鐵丹皺眉道:「剛剛才有結論,沒有神龍!」
司徒不凡笑道:「的確沒有神龍,但有一些人,卻比神龍更神通廣大,法力無邊!」
鐵丹心中一凜,問道:「你指的,是這一局的幕後主謀?公孫聞道?斗篷人?」
司徒不凡收起了嬉笑,神色變得肅穆,又坐下喝了一盞茶,才淡淡說道:「姑且稱之為神龍,亦無不可。」
提起斗篷人,秦弦月也覺心有餘悸,沉吟片刻,突然一咬牙,憤起說道:「既然不願幫忙,那便罷了,但我等卻不能坐以待斃!與其等死,倒不如唱一齣《戰洪州》,與司徒不平拼死一戰,或許還有一線生機!」
司徒不凡長嘆道:「就你二人,與司徒不平拼命?方才已經說了,什麼都不必做,你我三人,這一天都很安全,何苦等不及白白送死?」
秦弦月怒道:「本姑娘不想死,卻也做不到眼睜睜看著雲姑娘或小勺子去死!司徒不凡,你常說,天底下有兩種人,我秦弦月不如你,不是那種可以無情犧牲養了多年的忠犬、把人命視如草芥、把萬物當作芻狗之人!」她一頓,又轉頭忿忿問道:「臭皮蛋!你呢?你是哪一種人?」
「我?」鐵丹一揚眉,笑道:「我是膽子比拳頭還大之人,不怕鬼、不怕死,說到拼死一戰,更是拿手絕活!也罷,臭皮蛋混著鹹月餅吃,我就陪你,破一破這『洪州之圍』吧!」
秦弦月也還沒答話,司徒不凡聞言卻已坐不住了,忙攔住道:「別去、別去,拜託千萬別去。我沾了一身臭糞,才爭取來你兩個盟友,你們一死了之,我豈非白費工夫?」他無奈長長一聲怒嘆,接著道:「罷了、罷了,看在你二人為本公子解決了天命燈一大疑團,辦法倒有一個,只是說了出來,你們多半也不會喜歡。」
秦弦月見有轉機,忙道:「你說你的,我聽我的。」
司徒不凡聳了聳肩道:「很簡單,學長風劍,躲起來!只要在子時之前,別讓司徒不平找到便是。」
「躲?」鐵丹皺眉問道:「山莊說大不大,幾個大活人,躲得了嗎?」
司徒不凡嘴角一笑,說道:「按他的脾性,多半要到臨近子時,才會出手。山莊說小也不小,只要能躲得過半個時辰,便已足夠!」
鐵、秦二人對視一眼,皆覺可行,雖然還是很冒險,但比起與司徒不平拼命,卻似乎還是更有勝算。
「只不過,」司徒不凡也不等他二人答話,又說道:「你們不喜歡的部分,這就來了,你們還是得作一個選擇。雲菲語、小勺子、郭大膛,三人之中,你們必須排除一個!」
「那是為何?」
司徒不凡深吸了一口氣,解釋道:「給司徒不平留下一人,他有了後路,其他人躲過一晚的機會才會更大!」這就是兵法中「圍師必闕」的道理。他一頓,又接著道:「更何況,我說過了,躲得過司徒不平,也躲不過神龍。倘若當真沒有人獻祭,神龍為了實現公孫世叔說過的話,也必會奪取一人性命!本公子再提醒你們,這是一場針對我與司徒不平的局,千萬別天真以為可以把司徒不平拖下水,倘若由神龍作選擇,它的目標,絕對不會是我二人!所以與其如此,何不由你們自己決定?」
秦弦月聞言瞪圓了眼怒道:「由我們決定獻祭之人?那我們與司徒不平有什麼不一樣?」
司徒不凡苦笑道:「本來就沒什麼不一樣,我說了,這就是人性。或許,我一直以來都錯了,或許天底下,其實從來都只有一種人!」
鐵、秦二人怔怔發楞,滿腔不忿,卻良久說不出話。人為了保護自己、保護在乎之人,有些時候,就不得不犧牲一些無辜之人。這種行為,到底是義,還是不義?或許,義之一事,本來便沒有準則。道理確實如此,二人雖難以接受,但卻竟無言反駁,更無法提出更好的辦法。
司徒不凡似笑非笑,看著兩人天人掙扎的神情,問道:「那,你們會選擇誰呢?」
鐵丹長長嘆了口氣,說道:「不能是小勺子。他還很年輕。」
秦弦月也洩氣悵然道:「也不能是雲姑娘。這是我欠她的。」
司徒不凡一撫掌,笑道:「那便是郭大膛了。」
鐵丹疑道:「大湯鍋視他為恩公,對他言聽計從、畢恭畢敬,他能下得了手?」
「能。」司徒不凡不假思索,「到了關鍵時刻,他連老婆孩子都能犧牲。」
秦弦月也疑道:「你如此肯定?」
司徒不凡淡淡一笑,答道:「我絕對肯定,因為本公子也是這樣的人。分別只是,我從來不否認這一點!」
——
郭大膛雙目通紅,呼吸粗重,汗流浹背,渾身污泥,感覺全身力氣都已掏盡,卻還是不願停下歇息片刻。
他挺著鐵鏟,一鏟一鏟地把土地挖開,不停地挖、不停地挖。整個院子的青石地磚都已被掀翻,假花假草被連根拔起,房內的箱櫃被推翻,案几被掀倒,本來高雅堂皇的莊院如遭洗劫,滿目瘡痍,狼藉不堪。
他如此發了瘋似的搜尋長風劍,已將近一整天。搜完了一座院子,便又接著去搜另一座院子。雖然這的確是司徒不平的命令,但他卻似乎表現得特別賣力、特別拼命,這是因為怕死?還是出於對大公子的崇敬?還是其他的原因?
不過儘管已透支了渾身力量,他所搜尋過的範圍,卻也只不過是整座大千山莊的冰山一角而已。所以當子時一分一分地逼近,他也愈發心急如焚。他想加快手腳,但體力卻似已耗盡,就在他感到腦袋一陣暈眩之際,突然一隻手掌貼上背心,但覺一股暖流徐徐湧入體內,傳遍四肢百骸,頓時精神一振,如獲重生,同時身後更傳來一把沉穩的聲音,說道:「夠了,歇歇吧。」
郭大膛回過身來,抬頭一看,果然正是大公子。他一望四下亂狀,面帶慚色,垂頭嘆道:「大膛無能,白忙了一天,依舊不見長風劍蹤影。」不等對方答話,他又突然一愕,抬頭著急問道:「現在是什麼時辰了?」
司徒不平不動聲色,淡淡答道:「再過兩刻,便是子時了。」
郭大膛聞言一驚,慌道:「時間過得這麼快?這、這、這如何是好?」
司徒不平沒有答話,四下看了一眼,不見有其他人,才問道:「你一直在此掘地?」
「除了掘地,也掀了地磚、拔了花草、翻了箱子、還砸了不少瓶瓶罐罐。」
「你可有見到鐵丹、秦弦月、雲菲語、小勺子,或是,司徒不凡?」
「自早上離開七曜塔後,便不曾見過。他們想必,也在忙著四處搜尋?」
司徒不平知道郭大膛是個老實人,說的也是老實話,不由得輕嘆了一聲,感慨說道:「大膛呀大膛,你來到山莊日子也不短了,人緣就這麼差嗎?」
子時將至,卻一直沒有長風劍的消息,他果然如司徒不凡所料,出來尋找獻祭的人選。他本來屬意最年少無用、對他也甚是無禮的小勺子,但匆匆在山莊里轉了一圈,查看了每一座院子,四處卻一片死寂,看不見半個人影,直至到了此處,才看見了郭大膛。他心知肚明,眾人是早有預謀,躲起來了,只不過,卻偏偏留下了郭大膛,意思已是不言而喻。在這山莊裡,找幾個大活人當然比找一把劍容易許多,但時間緊急,卻已經來不及了。可嘆郭大膛這個老實人,卻還蒙在鼓裡,渾然不知。
即便此時話已說到這一份上,郭大膛也還是茫然不解,「大公子此話何意?」
司徒不平一揮衣袖,轉身道:「不說了,跟我走吧。」
「走?不、不挖了?」
「不挖了。」司徒不平邁開腳步,語帶悵然,嘆道:「你,再也不必挖了。」
——
司徒不平領著郭大膛,一路走回到七曜塔。踏入神龍閣,卻忽見一人負手佇立神龍石像之前,原來竟是司徒不凡。
司徒不平停下腳步,臉色一沉,問道:「你來此作甚?」
司徒不凡施施然轉過身來,臉帶微笑,說道:「子時將至,獻祭儀式即將開始,不凡自然是來觀禮的!」